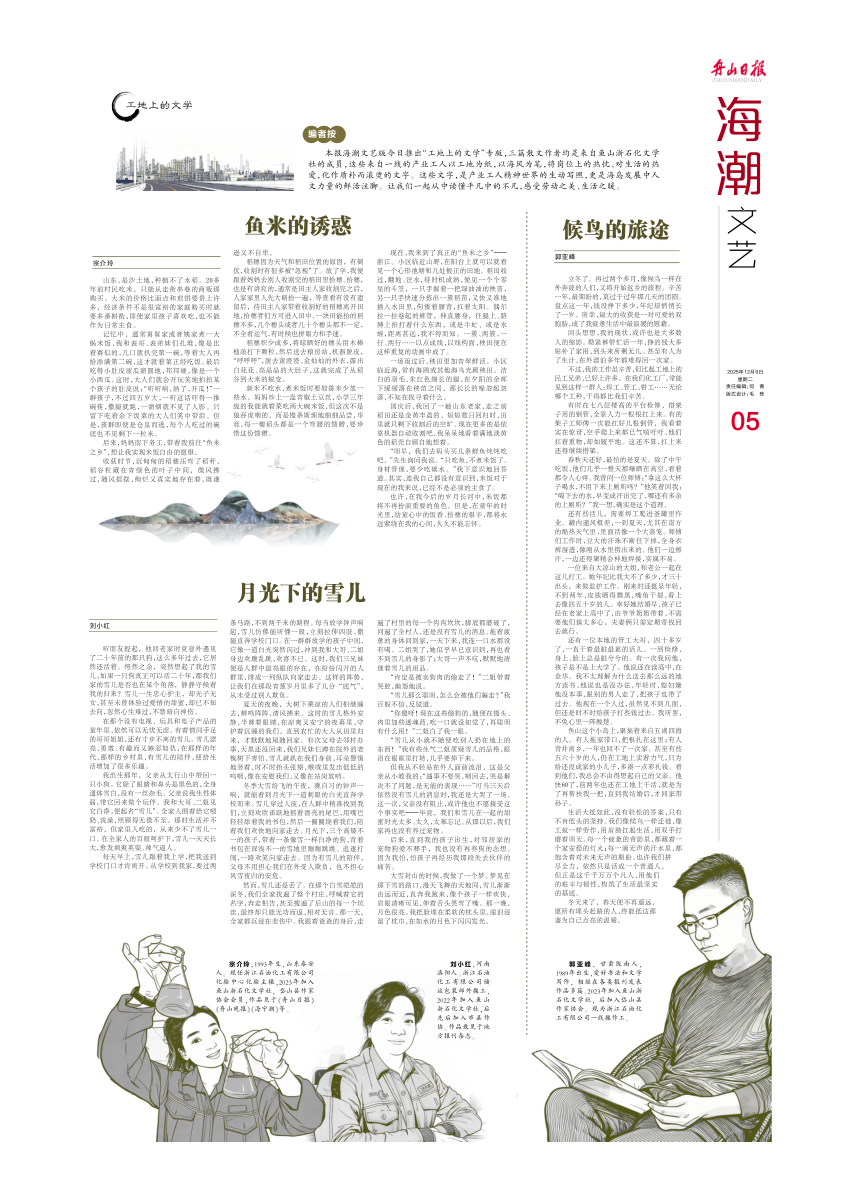工地上的文学
鱼米的诱惑
宗介玲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12月09日 第 05 版 )


山东,是沙土地,种植不了水稻。20多年前村民吃米,只能从走街串巷的商贩那购买。大米的价格比面点和煎饼要贵上许多,经济条件不是很富裕的家庭购买时就要多番斟酌,即使家里孩子喜欢吃,也不能作为日常主食。
记忆中,通常舅舅家或者姨家煮一大锅米饭,我和表哥、表弟妹们扎堆,像是比着赛似的,几口就扒完第一碗,等着大人再给添满第二碗,这才就着菜正经吃饭。最后吃得小肚皮滚瓜溜圆地,邦邦硬,像是一个小西瓜。这时,大人们就会开玩笑地拍拍某个孩子的肚皮说:“听听响,熟了,开瓜!”一群孩子,不过四五岁大,一听这话吓得一推碗筷,撒腿就跑,一溜烟就不见了人影。只留下吃着余下饭菜的大人们笑中带泪。但是,孩群即使是仓皇而逃,每个人吃过的碗底也不见剩下一粒米。
后来,妈妈南下务工,带着我前往“鱼米之乡”,想让我实现米饭自由的愿望。
收获时节,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稻谷粒藏在青绿色的叶子中间,微风拂过,随风摇摆,绚烂又真实地存在着,既谦逊又不自卑。
稻穗因为天气和稻田位置的原因,有倒伏,收割时有很多被“忽视”了。放了学,我便跟着妈妈去别人收割完的稻田里拾穗。拾穗,也是有讲究的,通常是田主人家收割完之后,人家家里人先大略拾一遍,等查看有没有遗留后,待田主人家带着收割好的稻穗离开田地,拾穗者们方可进入田中。一块田能拾的稻穗不多,几个穗头或者几十个穗头都不一定,不全看运气,有时候也拼眼力和手速。
稻穗积少成多,将晾晒好的穗头用木棒槌敲打下颗粒,然后送去粮房站,机器脱皮,“呼呼呼”,脱去黄澄澄、金灿灿的外衣,露出白花花、亮晶晶的大肚子,这就完成了从稻谷到大米的蜕变。
新米不吃水,煮米饭时要较陈米少放一些水。妈妈炒上一盘青椒土豆丝,小学三年级的我能就着菜吃两大碗米饭,但这次不是狼吞虎咽的,而是慢条斯理地细细品尝,毕竟,每一穗稻头都是一个弯腰的馈赠,要珍惜这份馈赠。
现在,我来到了真正的“鱼米之乡”——浙江。小区临近山野,在阳台上就可以就看见一个心形池塘和几处板正的田地。稻田收过,翻地、注水,待时机成熟,便见一个个零星的斗笠,一只手握着一把绿油油的秧苗,另一只手快速分拣出一簇稻苗,又快又准地插入水田里,佝偻着腰背,扛着太阳。偶尔拉一拉卷起的裤管,伸直腰身,往腿上、胳膊上拍打着什么东西,或是牛虻、或是水蛭,距离甚远,我不得而知。一簇、两簇,一行、两行……以点成线,以线构面,秧田便在这样重复的动画中成了。
一场雨过后,秧田更加青翠鲜活。小区临近海,常有海鸥或其他海鸟光顾秧田。洁白的羽毛、朱红色细长的腿,在夕阳的余晖下缓缓落在秧苗之间,那长长的喙忽起忽落,不知在找寻着什么。
国庆后,我回了一趟山东老家,走之前稻田还是金黄丰盈的,短短数日回归时,田里就只剩下收割后的空旷。现在更多的是依靠机器自动收割吧,我呆呆地看着满地淡黄色的稻壳自顾自地想着。
“明早,我们去码头买几条鲜鱼炖炖吃吧。”先生询问我说。“只吃鱼,不煮米饭了。身材管理,要少吃碳水。”我下意识地回答道。其实,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米饭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不是必须的主食了。
也许,在我今后的岁月长河中,米饭都将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童年的时光里,幼童心中的饭香、拾穗的艰辛,都将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