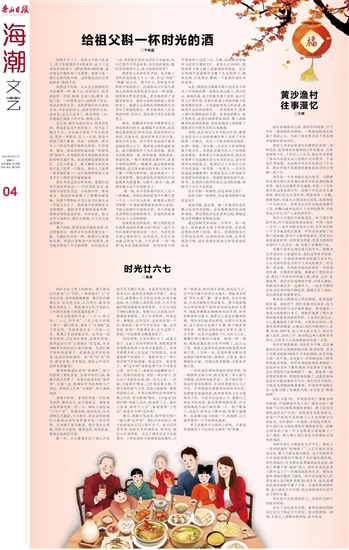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时光廿六七
鱼享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4年02月21日 第 04 版 )
□鱼享
站在小房子顶上的烟囱,顶上两块瓦片搭成“人”字状,一缕缕烟从“人”字里钻出来,轻轻慢慢地飘散。刚开始时细细长长、似有若无状,几分钟后,就显得粗实而稳定了,那是因为小房子里的大土灶膛里的柴火热情蓬勃起来了。
时光走到农历年前,“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年鸡”,土灶上的大铁锅上围了一圈白铁皮,就有了“大淘锅”这个新身份,里面煮的正是一刀肉一只鸡。耄耋之年的婆婆以为,过年是一定要有肉的,不仅要有猪肉,还要有鸡肉。猪肉是由它的“江湖地位”决定的,早在7000多年前的长江黄河流域,先民们就开始饲养家猪了,吃猪肉是营养的需要,也是富裕的象征。而“鸡”同“吉”同音,寓意吉利、吉祥如意,谁的心中没有这样的祈愿呢?
猪肉要挑最标准的“肋条肉”,每刀肉都要三条肋条宽。在菜市场开门前,婆婆早就去等着了。鸡要名副其实的“放养鸡”,立夏一过,她就向村里的养殖大户预定。煮肉的土灶和“大淘锅”,来自她的坚持。
婆婆年轻时,家里吃肉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哪怕过年,也不能保证。婆婆做姑娘时家里就一穷二白,嫁的人家也是“门当户对”。要地没地,要房没房,小夫妻俩白手起家,儿女渐长,居无定所的他们只能拿出多年的积蓄并举一部分外债,去向别人家买地基,然后再从头积蓄,争取早日造房。那些过往,每每说起,婆婆总是深深叹息。
那一年,公公婆婆听信了别人介绍的开采大理石生意,可是所有的投入都血本无归,家里简直要揭不开锅了。临近年关,婆婆乘公交车外出办事,结果车被追尾,车上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只有坐在最后排的婆婆肩颈骨骨折。公交公司给了300元赔偿款,要她自己去医院治疗。婆婆却拿着钱,买了年货和肉,回家过年。婆婆说,过年过年,过的其实是一个坎,图的是一家子平平安安在一起。过年有的,新的一年就都会有;过年过好了,新的一年也就都会顺遂美好了。
时光荏苒,儿女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又添了孙辈和曾孙辈,婆婆那原来觉得拥挤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了,原来不堪重负的土灶完成了历史使命,由美观的燃气灶接任了。婆婆享受了一阵子新式燃气灶的便捷,临近过年,却发愁了。煮“过年肉”显然是燃气灶不可承受之重。思忖再三,婆婆决定趁翻修房子,在二层楼房的东边,再搭一间小房子,在小房子里的东北角,砌一台大土灶。一开始,大家都不赞成,土灶要用柴火烧,干净方便的燃气不用,真是自找麻烦。婆婆却固执己见,专程去隔壁村请来同样古稀之年的“老式师傅”砌灶。《沙家浜》里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婆婆重修“土灶台”,却是专为煮“过年肉”。
那天,婆婆打电话来,招呼我们周六一起去煮“过年肉”。我们兴冲冲赶去,孩子的姑姑姑丈们已经忙开了,姑丈们负责杀鸡,姑姑们负责烧热水、拔鸡毛,他们大声说笑着,早忘了曾反对过土灶的重生。上好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调料,只用一锅清水,然后添火加柴,如同过日子,在不急不躁中经营天长地久。我最喜欢的是“管灶火洞”,搬一条小板凳,坐在灶膛前,不急不缓地往里添柴禾。柴禾是婆婆从山林里捡的干树枝和农田边折的艾蒿杆,烧起来飘散出植物特有的芳香,和肉的鲜香相互融合,闻着让人感觉松懈而温暖。曾孙辈们趁着放寒假,也都早早来报到,这个要往火边煨个红薯,那个喊着要啃鸡爪。刚学会走路的最小的曾孙,被人生中第一次见识这满肚子红火的大土灶,满嘴巴喷白烟的大淘锅,唬得一愣一愣的,被跑进跑出的小哥哥绊倒了,也忘记了哭。我爱人最喜欢的是揭开锅盖看肉煮熟了没,十分钟一次,急得外甥女搬出苏东坡的《猪肉颂》来: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一切的美好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每一锅都煮足两小时,揭开盖来,“穿云香气丹墀漫,急得神仙把手招”。留下我们每一家送年要用的那份,其余的肉就可以马上开吃。平常特别注重膳食结构和养生的,发誓赌咒要减肥的,此时都将筷子齐齐地伸向了肉。年前年后这段日子,婆婆自己却是不吃肉的,她有戒律需要执着,但不妨碍她成为最忙碌的那一个。到了餐桌上,也是忙着叫这个撕鸡翅,给那个递蘸料。也是嗓门最大的那一个,吆喝着,让大家照着同一个节奏律动起来。
老人家能有什么别的心思呢,不就是希望她的子子孙孙们总都有“肉”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