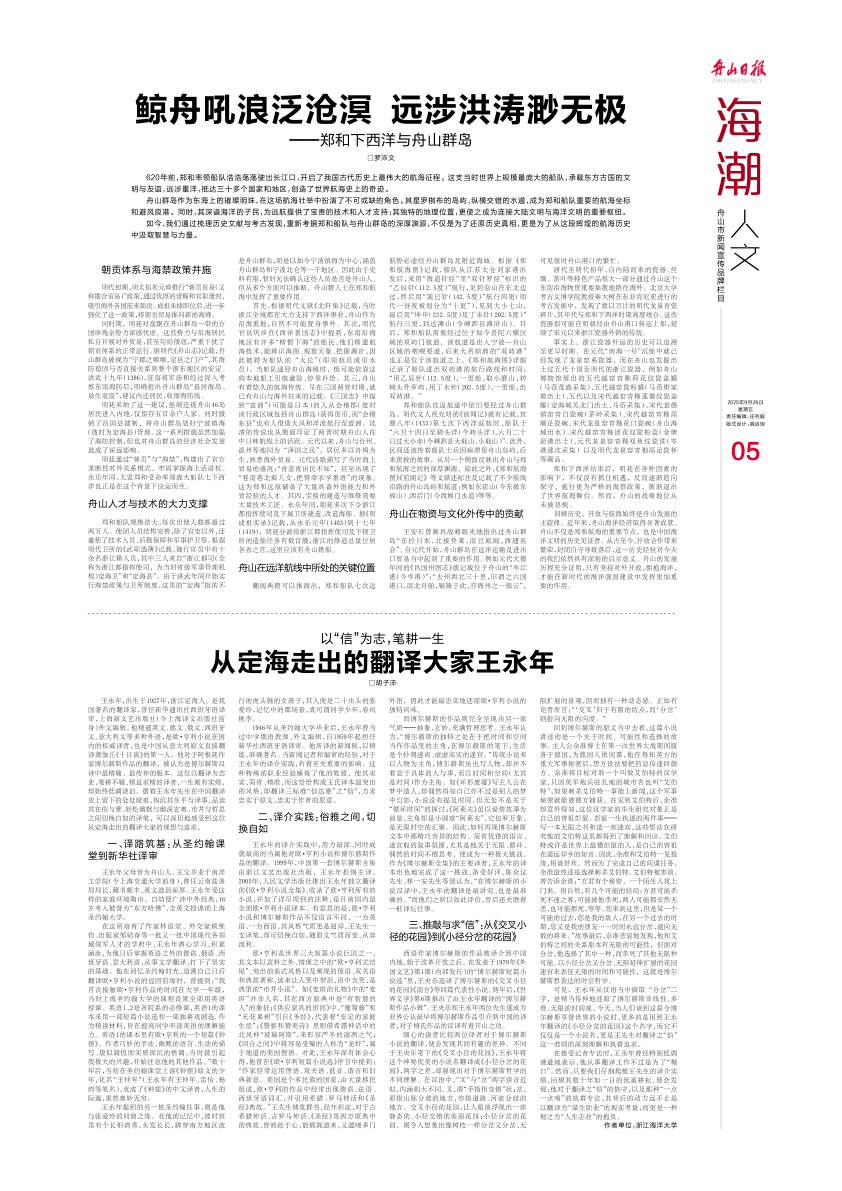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以“信”为志,笔耕一生
从定海走出的翻译大家王永年
胡子沛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09月26日 第 05 版 )
王永年,出生于1927年,浙江定海人。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曾任新华通讯社西班牙语译审,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今上海译文出版社前身)外文编辑。他精通英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是欧·亨利小说在国内的权威译者,也是中国从意大利原文直接翻译薄伽丘《十日谈》的第一人。他对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被认为是博尔赫斯汉译中最精确、最传神的版本。这位以翻译为志业,笔耕不辍、精益求精的译者,一生颇有实绩,却始终低调淡泊。循着王永年先生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的处处屐痕,钩沉其生平与译事,品读其在俗与雅、轻松幽默与幽深玄奥、市井与哲思之间切换自如的译笔,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位从定海走出的翻译大家的理想与追求。
一、译路筑基:从圣约翰课堂到新华社译审
王永年父母皆为舟山人。王父毕业于南洋工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曾任云南盐务局局长,藏书颇丰,英文造诣深厚。王永年受这样的家庭环境陶冶,自幼便广涉中外经典,16岁考入被誉为“东方哈佛”、全英文授课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在这所培育了作家林语堂、外交家顾维钧、出版家邹韬奋等一批又一批中国现代各领域领军人才的学府中,王永年潜心学习,积累涵泳,为他日后掌握英语之外的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回忆圣约翰时光、追溯自己日后翻译欧·亨利小说的远因前缘时,曾提到:“我首次接触欧·亨利作品的时间在大学一年级,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课程设置全部用英语授课。英语1、2是各院系的必修课,英语1的课本采用一部短篇小说选和一部独幕戏剧选,作为精读材料,旨在提高同学听读英语的理解能力。英语1的课本里有欧·亨利的一个短篇《钟摆》。作者巧妙的手法、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描写、貌似调侃而实质深沉的格调,当时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开始注意他的其他作品。”数十年后,当初在圣约翰课堂上读《钟摆》原文的少年,化名“王仲年”(王永年有王仲年、雷怡、杨绮等笔名),竟成了《钟摆》的中文译者,人生的际遇,果然奥妙无穷。
王永年提到的另一桩圣约翰往事,则是他与张爱玲的同窗之缘。在他的记忆中,彼时班里有个长相清秀,头发长长,脚穿南方地区流行的虎头鞋的女孩子,其人便是二十出头的张爱玲,记忆中的那场景,真可谓同学少年,春风桃李。
194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王永年曾当过中学俄语教师、外文编辑,自1959年起担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他所译的新闻稿,以精练、准确著名。当新闻记者和编审的经验,对于王永年的译介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特殊的职业经验锤炼了他的笔致,使其求实、简省、精准,而这恰恰构成王氏译本最突出的风格,即翻译三标准“信达雅”之“信”,力求忠实于原文,忠实于作者的原意。
二、译介实践:俗雅之间,切换自如
王永年的译介实践中,用力最深、同时成就最高的当属他对欧·亨利小说和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1999年,中国第一套博尔赫斯全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永年担纲主译。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永年独立翻译的《欧·亨利小说全集》,收录了欧·亨利所有的小说,并加了详尽周到的注释,是目前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译本。有意思的是,欧·亨利小说和博尔赫斯作品不仅语言不同,一为英语,一为西语,其风格气质更是迥异,王先生一支译笔,却可切换自如,随原文气质而变,从容流利。
欧·亨利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其文本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欧·亨利式结尾”、突出的美式风格以及频现的俚语、双关语和典故著称,读来让人笑中带泪,泪中含笑,是典型的“市井小说”。如《麦琪的礼物》中的“麦琪”并非人名,其在西方原典中是“有智慧的人”的象征;《供应家具的房间》中,“葡萄藤”和“无花果树”引自《圣经》,代表着“安定的家庭生活”;《警察和赞美诗》里则借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玻瑞阿斯”,来形容严冬的凛冽之气;《回合之间》中将容易受骗的人称为“龙虾”,属于地道的美国俚语。对此,王永年深有体会心得,他曾在《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序言中提到:“作家经常运用俚语、双关语、讹音、谐音和旧典新意。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大量移民组成,欧·亨利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词汇,并引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典故。”王先生博览群书,经年积淀,对于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圣经》等西方原典中的典故,皆熟稔于心,能娓娓道来,又通晓多门外语,因此才能最忠实地还原欧·亨利小说的独特风味。
而博尔赫斯的作品则完全呈现出另一派气质——抽象,玄妙,充满哲理思考。王永年认为,“博尔赫斯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时间和空间当作作品里的主角,在博尔赫斯的笔下,生活是个扑朔迷离、虚虚实实的迷宫。”传统小说多以人物为主角,博尔赫斯虽也写人物,却并不着意于具体的人与事,而以时间和空间(尤其是时间)作为主角。如《环形废墟》写主人公在梦中造人,却偶然得知自己亦不过是别人的梦中幻影,小说没有提及时间,但无处不是关于“循环时间”的探讨;《阿莱夫》虽以爱情故事为前景,主角却是小圆球“阿莱夫”,它包罗万象,是无限时空的汇聚。因此,如何再现博尔赫斯文本中那精巧奇异的结构、简省优雅的语言、迷宫般的叙事氛围,尤其是他关于无限、循环、偶然的时间不倦思考,便成为一种极大挑战。作为《博尔赫斯全集》的主要译者,王永年的译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挑战,备受好评,陈众议先生、林一安先生等便认为,“在博尔赫斯的小说汉译中,王永年的翻译是最讲究、也是最准确的。”而他们之所以如此评价,背后还关联着一桩译坛往事。
三、推敲与求“信”:从《交叉小径的花园》到《小径分岔的花园》
西语作家博尔赫斯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内地,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发表于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里,王央乐选译了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南方》等四篇代表性小说。两年后,《世界文学》第6期推出了由王永年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王央乐和王永年两位先生遂成为业界公认最早将博尔赫斯作品引介到中国的译者,对于博氏作品的汉译有着开山之功。
细心的读者比较两位译者对于博尔赫斯小说的翻译,便会发现其间有趣的差异。不同于王央乐笔下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王永年将这个神秘优美的小说名翻译成《小径分岔的花园》,两字之差,却展现出对于博尔赫斯哲学的不同理解。在汉语中,“叉”与“岔”两字读音近似,内涵则大不同。叉,谓“手指相交错”状;岔,原指山脉分歧的地方,亦指道路、河流分歧的地方。交叉小径的花园,让人眼前浮现出一座静态的、小径交错的美丽花园;小径分岔的花园,则令人想象出像树枝一样分岔又分岔、无限扩展的景观,因而独有一种动态感。正如有论者所言:“‘交叉’归于有限的结点,而‘分岔’则指向无限的向度。”
回到博尔赫斯的原文当中去看,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时间、可能性和选择的故事。主人公余准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德国,为德国人做间谍,他在得知英方的重大军事秘密后,想方设法要把信息传递回德方。余准将目标对准一个叫做艾伯特的汉学家,只因英军炮兵驻扎地的城市名也叫“艾伯特”,如果刺杀艾伯特一事能上新闻,这个军事秘密就能被德方捕获。在见到艾伯特后,余准却意外得知,这位汉学家的毕生研究对象正是自己的曾祖彭冣。彭冣一生执迷的两件事——写一本无限之书和造一座迷宫,这些想法在研究他的艾伯特这里都得到了理解和回应。艾伯特或许是世界上最懂彭冣的人,是自己的曾祖在遥远异乡的知音。因此,余准和艾伯特一见投缘,相谈甚欢。然而为了完成自己的间谍任务,余准最终还是选择刺杀艾伯特。艾伯特被害前,曾告诉余准:“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故事最后,余准悲哀地发现,他和艾伯特之间的关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但面对分岔,他选择了其中一种,而杀死了其他无限种可能。以小径分岔又分岔、无限延伸扩展的花园迷宫来表征无限的时间和可能性,这就是博尔赫斯想表达的时空哲学。
可见,王永年从汉语当中撷取“分岔”二字,是精当传神地还原了博尔赫斯非线性、多维、无限的时间观。今天,当人们谈到这篇令博尔赫斯享誉世界的小说时,更多的是用到王永年翻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名字,而它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名,更是王先生对翻译之“信”这一准则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永年曾经特别低调谦逊地表示,他从事翻译工作不过是为了“糊口”。然而,只要我们仔细爬梳王先生的译介实绩,回望其数十年如一日的伏案耕耘,便会发现:他对于翻译之“信”的恪守,以及那种“一点一点啃”的执着专注,其背后的动力远不止是以翻译为“谋生职业”的现实考量,而更是一种视之为“人生志业”的抱负。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