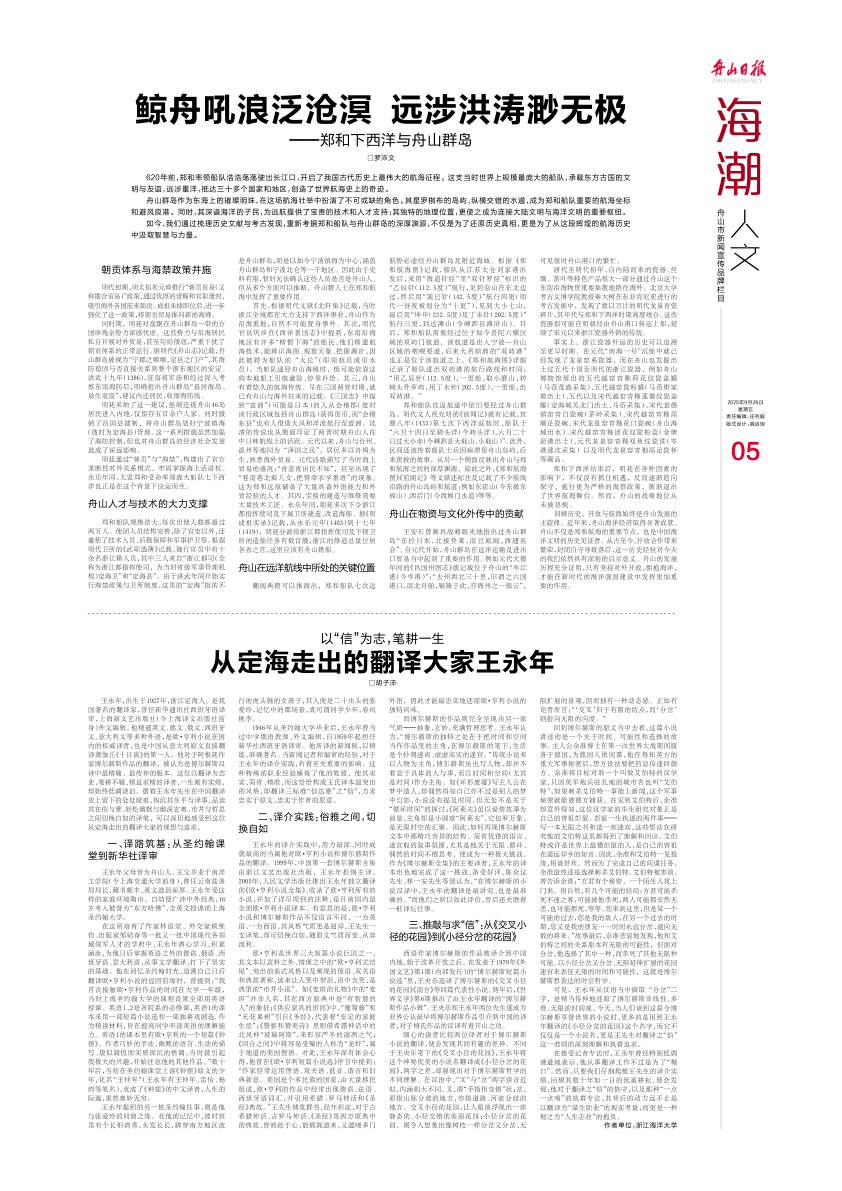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鲸舟吼浪泛沧溟 远涉洪涛渺无极
——郑和下西洋与舟山群岛
罗沛文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09月26日 第 05 版 )
620年前,郑和率领船队浩浩荡荡驶出长江口,开启了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征程。这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船队,承载东方古国的文明与友谊,远涉重洋,抵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舟山群岛作为东海上的璀璨明珠,在这场航海壮举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星罗棋布的岛屿、纵横交错的水道,成为郑和船队重要的航海坐标和避风良港。同时,其深谙海洋的子民,为远航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和人才支持;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使之成为连接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重要枢纽。
如今,我们通过梳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重新考据郑和船队与舟山群岛的深厚渊源,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从这段辉煌的航海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朝贡体系与海禁政策并施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推行“朝贡贸易(又称勘合贸易)”政策,通过优厚的赏赐和官职册封,吸引海外各国前来朝贡。成祖朱棣即位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将朝贡贸易推向新的高峰。
同时期,明廷对盘踞在舟山群岛一带的方国珍残余势力深感忧虑。这些势力与沿海居民私自开展对外贸易,甚至勾结倭寇,严重干扰了朝贡体系的正常运行。据明代《舟山志》记载,舟山群岛被视为“宁郡之咽喉,定邑之门户”,其海防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浙东地区的安定。洪武十九年(1386),征南将军汤和经过深入考察东南海防后,明确指出舟山群岛“悬居海岛、易生寇盗”,建议内迁居民,收缩海防线。
明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强制迁徙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仅留存五百余户人家。同时撤销了昌国县建制,将舟山群岛划归宁波镇海(彼时为定海县)管理。这一系列措施虽然加强了海防控制,但也对舟山群岛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明廷通过“朝贡”与“海禁”,构建出了官方垄断性对外关系模式,牢固掌握海上话语权。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受命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舟山人才与技术的大力支撑
郑和船队规模浩大,每次出使人数都超过两万人。使团人员结构完善,除了官吏以外,还囊括了技术人员、后勤保障和军事护卫等。根据明代卫所的《武职选簿》记载,随行官员中有十余名浙江籍人员,其中三人来自“浙江都司(全称为浙江都指挥使司,为当时省级军事管理机构)定海卫”和“定海县”。由于洪武年间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与卫所制度,这里的“定海”指的不是舟山群岛,而是以如今宁波镇海为中心,涵盖舟山群岛和宁波北仑等一干地区。因此由于史料有限,暂时无法确认这些人员是否是舟山人。但从多个方面可以推断,舟山籍人士在郑和航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根据明代文献《北轩集》记载,当时浙江全境都在大力支持下西洋事业,舟山作为沿海重地,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其次,明代官员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提到,东南沿海地区有许多“精惯下海”的船民,他们精通航海技术,能辨识海图、观察天象、把握潮汐,因此被聘为船队的“火长”(即领航员或引水员)。当船队途经舟山海域时,极可能依靠这些本地船工引航避险、停靠补给。其三,舟山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就已有舟山与海外往来的记载。《三国志》中提到“亶洲”(可能是日本)的人从会稽郡(彼时该行政区域包括舟山群岛)获得货币,而“会稽东县”也有人借助大风和洋流航行至亶洲。沈清的传说也从侧面印证了两晋时期舟山人在中日韩航线上的活跃。元代以来,舟山与台州、温州等地同为“泽国之民”,居民多以舟楫为生,熟悉海外贸易。元代诗歌描写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盛况:“青盖夜出民不知”,甚至出现了“巷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番语”的现象。这为郑和远航储备了大量具备外语能力和外贸经验的人才。其四,宝船的建造与维修需要大量技术工匠。永乐年间,朝廷多次下令浙江都指挥使司及下属卫所建造、改造海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从永乐元年(1403)到十七年(1419),明廷分派给浙江都指挥使司及下辖卫所的造船任务有数百艘,浙江的修造总量位居各省之首,这里应该有舟山籍船。
舟山在远洋航线中所处的关键位置
翻阅典籍可以推测出,郑和船队七次远航势必途经舟山群岛及附近海域。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后,采用“海道针经”里“双针罗经”标识的“乙辰针(112.5度)”航行,见到佘山在东北边过,然后用“巽巳针(142.5度)”航行四更(明代一昼夜被划分为“十更”),见到大小七山,最后用“坤申(232.5度)及丁未针(202.5度)”航行三更,到达滩山(今嵊泗县滩浒山)。其后,郑和船队需要经过位于如今普陀六横区域的双屿门航道,该航道是出入宁波—舟山区域的咽喉要道,后来大名鼎鼎的“双屿港”也正是位于该航道之上。《郑和航海图》详细记录了船队进出双屿港的航行路线和时间:“用乙辰针(112.5度),一更船,取小磨山,转崎头升罗屿,用丁未针(202.5度),一更船,出双屿港。”
郑和船队在返航途中依旧要经过舟山群岛。明代文人祝允明的《前闻记》就有记载,宣德八年(1433)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时,船队于“六月十四日至骑头洋(今峙头洋),六月二十日过大小赤(今嵊泗县大戢山、小戢山)”。此外,民间还流传着船队士兵因病滞留舟山岛屿,后来获救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舟山与郑和航海之间的深厚渊源。除此之外,《郑和航海图》《前闻记》等文献还标注及记载了不少航线沿路的舟山岛屿和航道:例如东霍山(今东极东福山)、西后门(今西堠门水道)等等。
舟山在物资与文化外传中的贡献
王安石曾颇具战略眼光地指出过舟山群岛“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自元代开始,舟山群岛在远洋运输及进出口贸易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元代大德年间的《昌国州图志》就记载位于舟山的“岑江港(今岑港)”:“去州西北三十里,旧谓之六国港口,南北舟舶,辐辏于此,亦海州之一镇云”,可见彼时舟山港口的繁忙。
唐代至明代初年,自内陆而来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特色产品很大一部分通过舟山这个东南沿海物资重要集散地销往海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在东非肯尼亚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明代龙泉青瓷碎片,其年代与郑和下西洋时期高度吻合。这些瓷器很可能在明朝经由舟山港口转运上船,延续了宋元以来浙江瓷器外销的传统。
事实上,浙江瓷器外运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在元代“南海一号”沉船中就已经发现了龙泉窑系瓷器,而在舟山也发掘出土过五代十国至明代的浙江瓷器,例如舟山博物馆展出的五代越窑青釉荷花纹瓷盖罐(马岙茂盛采集)、五代越窑瓷粉罐(马岙唐家墩出土)、五代以及宋代越窑青釉莲瓣纹瓷盖罐(定海城关北门出土、马岙采集)、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碗(茅岭采集)、宋代越窑青釉高圈足瓷碗、宋代龙泉窑青釉花口瓷碗(舟山海域出水)、宋代越窑青釉团花纹瓷粉盒(金塘沥港出土)、元代龙泉窑青釉双鱼纹瓷洗(岑港涨次采集)以及明代龙泉窑青釉高足瓷杯等藏品。
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廷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仅没有抓住机遇,反而逐渐趋向保守,施行更为严格的海禁政策,渐渐退出了世界航海舞台。然而,舟山的战略地位从未被忽视。
回顾历史,开放与航海始终是舟山发展的主旋律。近年来,舟山海洋经济取得显著成就。舟山不仅是郑和航海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者。从古至今,开放合作带来繁荣,封闭自守导致落后,这一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舟山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拥抱海洋,才能在新时代的海洋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