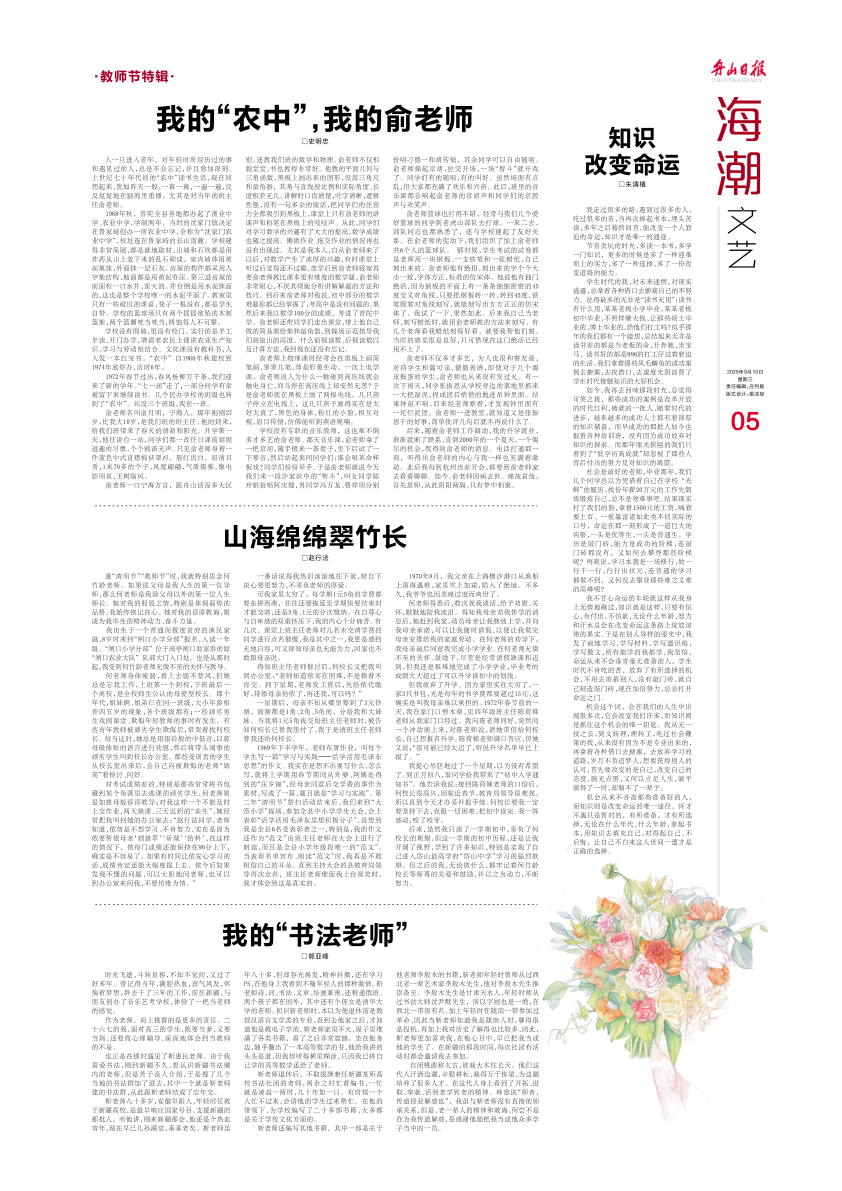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我的“农中”,我的俞老师
史明忠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09月10日 第 05 版 )
人一旦进入老年,对年轻时所经历过的事和遇见过的人,总是不会忘记,并且愈加深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农中”读书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犹如昨天一般,一幕一幕,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地在脑海里重播,尤其是对当年的班主任俞老师。
1968年秋,普陀全县各地都办起了渔业中学、农业中学,学制两年。当时的沈家门镇决定在鲁家峙创办一所农业中学,全称为“沈家门农业中学”,校址选在鲁家峙的长山南麓。学校建得非常简陋,都是就地取材,山墙和石坎都是用炸药从山上轰下来的乱石砌成,室内墙体用黄泥填抹,外面抹一层石灰。房屋的构件都采用人字架结构,地面都是用黄泥夯压。第三进房屋的前面有一口水井,蛮大的。井台倒是用水泥抹面的,这也是整个学校唯一的水泥平面了。教室里只有一些破旧的课桌,凳子一根没有,都是学生自带。学校的篮球场只有两个摇摇欲坠的木制篮架,两个篮圈咣当咣当,锈蚀得人不可攀。
学校没有围墙,更没有校门。实行的是半工半读,开门办学,聘请老农民上课讲农业生产知识,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文化课没有教科书,人人发一本红宝书。“农中”自1968年秋建校到1974年底停办,历时6年。
1972年春节过出,春风杨柳万千条,我们迎来了新的学年。“七一届”走了,一部分同学有幸被留下来继续读书。几个民办学校的班级也转到了“农中”。共设三个班级,我在一班。
俞老师名叫俞月明,宁海人,那年刚刚27岁,比我大10岁,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他的到来,给我们班带来了春天的清新和阳光。开学第一天,他往讲台一站,同学们都一改往日课前嬉闹逗趣的习惯,个个鸦雀无声。只见俞老师身着一件蓝色中式直襟棉袄罩衫,唇红齿白,眉清目秀,1米70多的个子,风度翩翩,气质儒雅,像电影明星,玉树临风。
俞老师一口宁海方言,跟舟山话没多大区别。还教我们班的数学和物理。俞老师不仅相貌堂堂,书也教得非常好。他教的平面几何与三角函数,黑板上画出来的图形,没用三角尺和量角器,其角与直线按比例和实际角度、长度相差无几。讲解时口齿清楚,吐字清晰,逻辑性强,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黑板上,课堂上只有俞老师的讲课声和粉笔在黑板上的吱吱声。从此,同学们对学习数学的兴趣有了大大的提高,数学成绩也随之提高。懒做作业、拖交作业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尤其是我本人,自从俞老师来了以后,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课堂上听过后觉得还不过瘾,放学后到俞老师寝室再要俞老师教比课本更有难度的数学题,俞老师非常耐心,不厌其烦地分析讲解解题的方法和技巧。到后来俞老师对我说,初中部分的数学难题你都已经掌握了,考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果然后来我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进了普陀中学。俞老师还带同学们走出课堂,带上他自己做的简易测绘架和量角器,到操场示范指导我们测量山的高度。什么前视读数、后视读数以及计算方法,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
俞老师上物理课时经常会在黑板上画简笔画,寥寥几笔,却是形象生动。一次上电学课,俞老师说人为什么一触碰到高压线就会触电身亡,而鸟停在高压线上却安然无恙?于是俞老师就在黑板上画了两根电线,几只燕子停立在电线上,这几只燕子画得实在是太好太真了,黑色的身体,粉红的小脸,相互对视,眉目传情,仿佛能听到燕语呢喃。
学校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这也难不倒多才多艺的俞老师。那天音乐课,俞老师拿了一把京胡,随手掇来一条凳子,坐下后试了一下琴音,然后站起来问同学们:谁会唱革命样板戏?同学们纷纷举手。于是俞老师就说今天我们来一段沙家浜中的“智斗”,叫女同学陈玲娟扮唱阿庆嫂,男同学冯万龙、费祥明分别扮唱刁德一和胡传魁,其余同学可以自由随唱。俞老师操起京胡,拉完开场,一场“智斗”就开戏了。同学们有的随唱,有的叫好。虽然场面有点乱,但大家都充满了欢乐和兴奋。此后,班里的音乐课都会响起俞老师的京胡声和同学们的京腔声与欢笑声。
俞老师篮球也打得不错,经常与我们几个爱好篮球的同学到老虎山部队去打球。一来二去,部队同志也都熟悉了,还与学校建起了友好关系。在俞老师的促动下,我们组织了加上俞老师共6个人的篮球队。那时候,学生考试的试卷都是老师用一块钢板、一支铁笔和一张蜡纸,自己刻出来的。俞老师他有绝招,刻出来的字个个大小一致,字体方正,标准的仿宋体。他说他有独门绝活,因为钢板的平面上有一条条细细密密的45度交叉对角线,只要把钢板转一转,转到45度,铁笔顺着对角线刻写,就能刻写出方方正正的仿宋体了。我试了一下,果然如此。后来我自己当老师,刻写蜡纸时,就用俞老师教的方法来刻写。有几个老师看我蜡纸刻得好看,就要我帮他们刻。当时的感觉很是良好,只可惜现在这门绝活已经用不上了。
俞老师不仅多才多艺,为人也很和善友爱,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即使对于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俞老师也从来没有发过火。有一次下雨天,同学张振恩从学校旁边的菜地里抓来一大把湿泥,捏成团后悄悄的抛进吊钟里面。结果钟敲不响,后来经老师察看,才发现钟里面有一坨烂泥团。俞老师一进教室,就知道又是张振恩干的好事,简单批评几句后就不再说什么了。
后来,随着俞老师工作调动,我的升学就业,渐渐就断了联系,直到2000年的一个夏天,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得到俞老师的消息。电话打通那一刻,听得出俞老师的内心与我一样也充满着激动。此后我每到杭州出差开会,都要到俞老师家去看看聊聊。如今,俞老师因病去世。痛哉哀哉,吾失恩师,从此阴阳两隔,只有梦中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