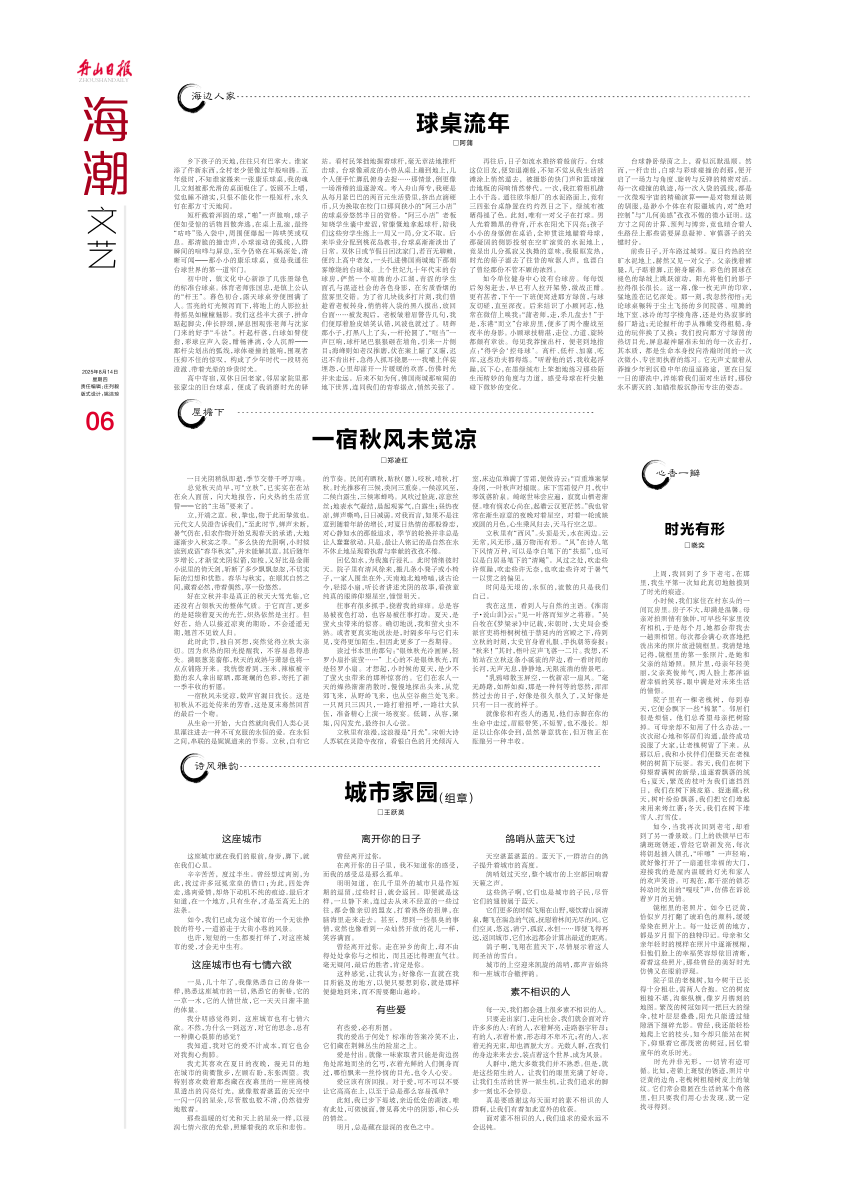屋檐下
一宿秋风未觉凉
郑凌红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08月14日 第 06 版 )
一日光阴稍纵即逝,季节交替千呼万唤。
总觉秋天尚早,可“立秋”,已实实在在站在众人面前,向大地报告,向火热的生活宣誓——它的“主场”要来了。
立,开端之意。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敛也。元代文人吴澄告诉我们,“至此时节,蝉声未断,暑气仍在,但农作物开始兑现春天的承诺,大地逐渐步入秋实之季。”多么快的光阴啊,小时候读到成语“春华秋实”,并未能解其意。其后随年岁增长,才渐觉光阴似箭,如梭,又好比是金庸小说里的倚天剑,斩断了多少飘飘忽忽,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忧愁。春华与秋实,在顺其自然之间,藏着必然,带着偶然,享一份悠然。
好在立秋并非是真正的秋天大驾光临,它还没有占领秋天的整体气质。于它而言,更多的是延续着夏天的光芒,炽热依然是主打。但好在,给人以接近凉爽的期盼,不会遥遥无期,翘首不见故人归。
此时此节,独自冥想,突然觉得立秋太亲切。因为炽热的阳光提醒我,不容易患得患失。满眼葱茏蓊郁,秋天的成熟与萧瑟也将一点点铺陈开来。我恍惚看到,玉米、辣椒被辛勤的农人拿出晾晒,那斑斓的色彩,寄托了新一季丰收的祈愿。
一宿秋风未觉凉,数声宫漏日犹长。这是初秋从不远处传来的芳香,这是夏末蓦然回首的最后一个吻。
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人类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在永恒之间,串联的是娓娓道来的节奏。立秋,自有它的节奏。民间有晒秋,贴秋(膘),咬秋,啃秋,打秋。时光推移有三候,类同三重奏。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风吹过脸庞,凉意丝丝;地表水气凝结,晨起观雾气,白露生;昼热夜凉,蝉声嘶鸣,日日减弱。对我而言,如果不是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夏日热情的那般眷恋,对心静如水的那般追求,季节的轮换并非总是让人蠢蠢欲动。只是,最让人铭记的是自然在永不休止地呈现着执着与奉献的孜孜不倦。
回忆如水,为我施行浸礼。此时情绪彼时天。院子里有清风徐来,搬几条小凳子或小椅子,一家人围坐在外,天南地北地唠嗑,谈古论今,轻摇小扇,听长者讲述光阴的故事,看孩童纯真的眼眸仰望星空,憧憬明天。
往事有很多抓手,挠着我的痒痒。总是容易被夜色打动,也容易被往事打动。夏天,是萤火虫带来的惊喜。确切地说,我和萤火虫不熟。或者更真实地说法是,时隔多年与它们未见,变得更加陌生,但因此更多了一些期待。
读过书本里的那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上心的不是银烛秋光,而是轻罗小扇。才想起,小时候的夏天,是少不了萤火虫带来的那种惊喜的。它们在农人一天的燥热渐渐消散时,慢慢地探出头来,从荒郊飞来,从野岭飞来,也从空谷幽兰处飞来。一只两只三四只,一路打着招呼,一路壮大队伍,准备精心上演一场夜宴。低调,从容,聚集,闪闪发光,最终扣人心弦。
立秋里有浪漫,这浪漫是“月光”。宋朝大诗人苏轼在灵隐寺夜宿,看银白色的月光倾泻入室,床边似堆满了雪霜,便做诗云:“百重堆案掣身闲,一叶秋声对榻眠。床下雪霜侵户月,枕中琴筑落阶泉。崎岖世味尝应遍,寂寞山栖老渐便。唯有悯农心尚在,起瞻云汉更茫然。”我也常常在渐生凉意的夜晚对着星空,对着一轮或缺或圆的月色,心生乘风归去,天马行空之思。
立秋里有“西风”。头顶是天,水在两边。云无常,风无形,遇万物而有形。“风”在诗人笔下风情万种,可以是李白笔下的“扶摇”,也可以是白居易笔下的“清飚”。风过之处,吹走些许烦躁,吹走些许无奈,也吹走些许对于暑气一以贯之的偏见。
时间是无垠的,永恒的,流散的只是我们自己。
我在这里,看到人与自然的主语。《淮南子·说山训》云:“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宋朝时,太史局会委派官吏将梧桐树植于禁廷内的宫殿之下,待到立秋的时刻,太史官身着礼服、手执朝笏奏报:“秋来!”其时,梧叶应声飞落一二片。我想,不妨站在立秋这条小溪流的岸边,看一看时间的长河,无声无息,静静地,无限流淌的情景吧。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毫无踌躇,如醉如痴,那是一种何等的悠然,浑浑然过去的日子,好像是很久很久了,又好像是只有一日一夜的样子。
就像你和有些人的遇见,他们赤脚在你的生命中走过,眉眼带笑,不短暂,也不漫长。却足以让你体会到,虽然暑意犹在,但万物正在酝酿另一种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