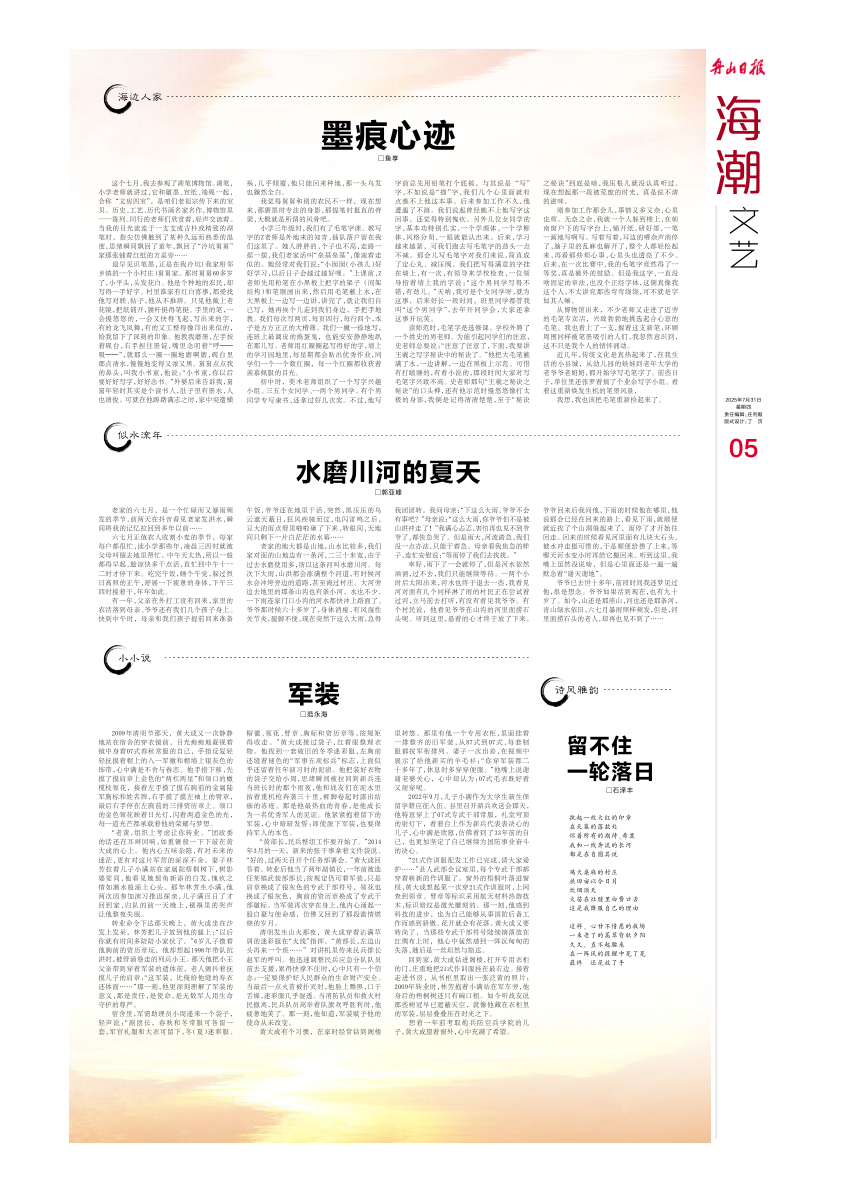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墨痕心迹
鱼享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07月31日 第 05 版 )
这个七月,我去参观了湖笔博物馆。湖笔,小学老师就讲过,它和徽墨、宣纸、端砚一起,合称“文房四宝”,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历史、工艺、历代书画名家名作,博物馆里一一陈列。同行的老师们欣赏着,轻声交流着。当我的目光流连于一支支或古朴或精致的湖笔时,指尖仿佛触到了某种久远而熟悉的温度,思绪瞬间飘回了童年,飘回了“冷坑舅舅”家那张铺着红纸的方桌旁……
最早见识笔墨,正是在我冷坑(我家相邻乡镇的一个小村庄)舅舅家。那时舅舅60多岁了,小平头,头发花白。他是个种地的农民,却写得一手好字。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爱找他写对联、帖子,他从不推辞。只见他戴上老花镜,把纸铺开,腰杆挺得笔挺。手里的笔,一会慢悠悠的,一会又快得飞起,写出来的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又工整得像印出来似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我磨墨,左手按着砚台,右手捏住墨锭,嘴里念叨着“呼———吸———”,就那么一圈一圈地磨啊磨,砚台里那点清水,慢慢地变得又浓又黑。舅舅点点我的鼻头,叫我小书童,他说:“小书童,你以后要好好写字,好好念书。”外婆后来告诉我,舅舅年轻时其实是个读书人,肚子里有墨水,人也清俊。可就在他踌躇满志之时,家中突遭横祸,几乎倾覆,他只能回来种地,那一头乌发也骤然全白。
我觉得舅舅和别的农民不一样,现在想来,那磨墨时专注的身影,那提笔时挺直的脊梁,大概就是所谓的风骨吧。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有了毛笔字课。教写字的Z老师是外地来的知青,插队落户留在我们这里了。她人胖胖的,个子也不高,走路一摇一摆,我们老家话叫“垒基垒基”,像滚着走似的。她经常对我们说:“小囡囡(小孩儿)好好学习,以后日子会越过越好哩。”上课前,Z老师先用粉笔在小黑板上把字的架子(间架结构)和笔顺画出来,然后用毛笔蘸上水,在大黑板上一边写一边讲,讲完了,就让我们自己写,她再挨个儿走到我们身边,手把手地教。我们每次写两页,每页四行,每行四个,本子是方方正正的大楷簿。我们一撇一捺地写,连班上最调皮的捣蛋鬼,也能安安静静地趴在那儿写。老师用红圈圈起写得好的字,墙上的学习园地里,每星期都会贴出优秀作业,同学们一个一个数红圈,每一个红圈都收获着羡慕佩服的目光。
初中时,美术老师组织了一个写字兴趣小组。三五个女同学、一两个男同学。有个男同学专写隶书,还拿过好几次奖。不过,他写字前总先用铅笔打个底稿,与其说是“写”字,不如说是“描”字,我们几个心里面就有点瞧不上他这本事。后来参加工作不久,他遭遇了不测。我们说起曾经瞧不上他写字这回事,还觉得特别愧疚。另外几位女同学的字,基本功特别扎实,一个学颜体,一个学柳体,风格分明,一眼就能认出来。后来,学习越来越紧,可我们跑去写毛笔字的劲头一点不减。那会儿写毛笔字对我们来说,简直成了定心丸、减压阀。我们把写得满意的字挂在墙上,有一次,有领导来学校检查,一位领导指着墙上我的字说:“这个男同学写得不错,有劲儿。”天呐,我可是个女同学呀,就为这事,后来好长一段时间,班里同学都管我叫“这个男同学”,去年开同学会,大家还拿这事开玩笑。
读师范时,毛笔字是选修课。学校外聘了一个姓史的男老师。为能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史老师总要说:“注意了注意了,下面,我要讲王羲之写字秘诀中的秘诀了。”他把大毛笔蘸满了水,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示范。可惜有打瞌睡的,有看小说的,那段时间大家对写毛笔字兴致不高。史老师那句“王羲之秘诀之秘诀”的口头禅,还有他示范时慢悠悠像打太极的身影,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至于“秘诀之秘诀”到底是啥,我压根儿就没认真听过。现在想起那一段被荒废的时光,真是说不清的滋味。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事情又多又杂,心里也烦。无奈之余,我就一个人躲到楼上,在朝南窗户下的写字台上,铺开纸,研好墨,一笔一画地写啊写。写着写着,耳边的嘈杂声消停了,脑子里的乱麻也解开了,整个人都轻松起来,再看那些烦心事,心里头也透亮了不少。后来,在一次比赛中,我的毛笔字竟然得了一等奖,真是额外的鼓励。但是我这字,一直没啥固定的章法,也没个正经字体,这倒真像我这个人,不太讲究那些弯弯绕绕,可不就是字如其人嘛。
从博物馆出来,不少老师又走进了近旁的毛笔专卖店,兴致勃勃地挑选起合心意的毛笔。我也看上了一支,握着这支新笔,环顾周围同样被笔墨吸引的人们,我忽然意识到,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情怀涌动。
近几年,传统文化是真热起来了,在我生活的小县城,从幼儿园的娃娃到老年大学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开始学写毛笔字了。前些日子,单位里还张罗着搞了个业余写字小组。看着这重新焕发生机的笔墨风景,
我想,我也该把毛笔重新捡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