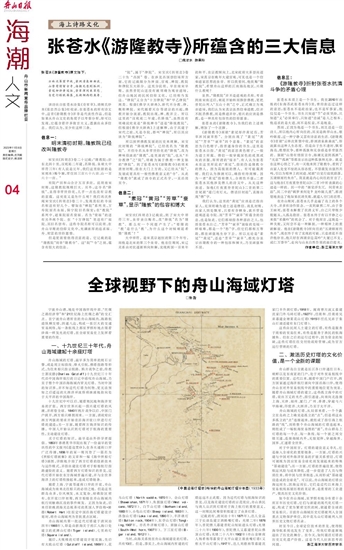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张苍水《游隆教寺》所蕴含的三大信息
倪浓水 陈燕玲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3年11月08日 第 04 版 )
□倪浓水 陈燕玲
张苍水《游隆教寺》原文如下:
云林次第望中收,碧涧清泉曲曲流。
山势有情留古寺,海潮无意到孤洲。
素冠却许黄冠伍,芳草浑同衰草愁。
自觉行踪犹廓落,五湖烟雨钓鱼舟。
该诗出自张苍水诗集《奇零草》,清傅氏钞本《张忠烈公集》有收录。在张苍水的所有诗文中,这首《游隆教寺》并非是代表性作品,但是如果从舟山文史的角度予以考察分析,却可以发现,它蕴含着许多微言大义,透露出众多信息。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三条。
信息一:
明末清初时期,隆教院已经改叫隆教寺
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记载:“隆教院:县东北四十里,汉乾祐二年建,名降钱。皇朝大中祥符三年(有人说是元年,我们这里依据的是宋刻本)赐今额,常住田三百六十六亩、山一百六十一亩。”
有院产田和山合计五百多亩,说明南宋时期,这隆教院规模巨大。另外,这寺名“降钱”,显得非常世俗化,几乎一点也没有宗教的意蕴。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再次查阅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发现类似的寺庙名称还有好几个。譬如在“禅院”系列里,万寿院原名永福,保宁院旧名保安;在“教院”系列中,超果院原名资福。名为“资福”的还有另外两个院。在“十方律院”里还有广福院,其旧名崇寿。这些寺院名称可以说明,在舟山早期的信仰文化中,充满浓厚的追求福、寿、财富的世俗愿望。
但是更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它记载的是“隆教院”而非“隆教寺”。这“院”“寺”之别,蕴含有很大的信息。
“院”,属于“律院”。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为“昌国”卷。在涉及昌国崇信场所方面,它的记载细分为神庙、宫观、禅院、教院和律院五大部分。这充分说明,早在南宋早期,虽然普陀山还没有被明确为观音道场,但舟山地区的民间信仰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律院”又分为“十方律院”和“甲乙律院”两类。根据《佛学大辞典》,唐代不分教、律,概称禅院。宋代随着天台等诸宗的兴起,佛教开始分流派,教院出现,禅、教并立。所以这里的“汉乾祐二年建,名降钱”,虽然没有明确说究竟是“降钱禅寺”还是“降钱教院”,但根据《佛学大辞典》上述解释,由于其建于宋代之前,凡是寺院,都叫“禅院”,所以其应该为“降钱禅院”。
所以按照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理解,宋宝庆时期的“降钱禅院”,已经改名为“隆教院”。不但寺名从非常世俗化的“降钱”,改为禅味很浓的“隆教”,连里面的“院”,也从“不分教律”之“院”,明确为属于佛教一种支脉的“律院”。到了张苍水写《游隆教寺》的明末清初时期,挂在大门上方的,又已经从“院”,发展成更具有一般性佛教意义的“寺”。从此“隆教寺”就成了该寺的正式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信息二:
“素冠”“黄冠”“芳草”“衰草”,显示“隆教”的包容和博大
宋宝庆《四明志》记载说,到了宋大中祥符三年,皇帝亲自赐名,改“降钱”名为“隆教”。那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要隆的‘教’是什么‘教’,为什么这个时候朝廷希望‘隆教’?”
大中祥符,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个年号,而他是北宋的第三个皇帝。他在位期间,宋辽关系由对抗逐渐转向和解,实现两国一百来年的和平。在宗教倾向上,北宋政府大多崇尚道家,宋真宗在晚年大建宫观,可见也是一个信奉道家思想的皇帝。所以我要问,他钦赐“隆教院”,希望舟山这样的江南海岛地区,兴隆什么教呢?
显然,“隆教院”并不是道观的名称。考虑到南宋南迁后,朝廷开始转而推崇佛教,更把普陀山列入“五山十刹”之中,正式确立为观音道场,我们认为宋真宗虽然信奉道教,但并不扼杀佛教,而是佛道并存,要兴的应该是佛教,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信仰愿景。
张苍水的《游隆教寺》,为我们的上述理解,增加了一个注脚。
《游隆教寺》颈联“素冠却许黄冠伍,芳草浑同衰草愁”,分别出现了“素冠”“黄冠”“芳草”“衰草”四个意象。“素冠”的意思为白色帽子,指普通身份的书生,这里是张苍水自指。“黄冠”的意思黄色帽子,一般为道士所戴。僧侣一般穿戴深色的或黑或灰的衣服,即所谓的“缁衣”。有人认为张苍水在这里所说的“黄冠”,指的仍是隆教寺的僧人,因为高级别的僧人,有可能戴黄帽。我们认为推测可以,确指有待商榷。因为一者“黄冠”指称僧人,合理性不强;二者张苍水其他涉及僧人的诗文中,从无这种表述。如他《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的第二首尾联“迎门有灯火, 僧话旧时踪”,直接出现“僧”字。
我们认为,这里的“黄冠”应该是泛指出家人,无须明确为道士还是僧侣。战乱时期,出家人四处飘零,只要有舍栖身,就不管是道观还是寺院。而“芳草”“衰草”所蕴含的信息,也是如此。它们都暗指各种漂泊之人,包括张苍水自己。“芳草”“衰草”面临的处境一样艰难,都是一个“愁”字,但它们都相互帮助,都在顽强地生存下去。所以无论是“素冠”“黄冠”,还是“芳草”“衰草”,都充分显示出隆教寺的一种包容和博大,乃至顽强和不屈。
信息三:
《游隆教寺》折射张苍水抗清斗争的矛盾心理
张苍水本质上是一个书生。我在2010年出版的《东海苏武张苍水传》里,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张苍水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他仅仅是一个书生。书生只知道“节”必须坚持,只知道“义”必须奉行,只知道“忠诚”是人之根本。他追求的是大道,而不是权益,不是地盘。
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个书生,而且还是一位诗人,所以他内心所向往的,其实是徜徉山水,歌吟烟霞,过一种宁静又富有诗意的生活。《游隆教寺》首联“云林次第望中收,碧涧清泉曲曲流”,即流露出这种人生态度。但是由于生不逢时,飘零海岛,绝望抗争,那种孤独和无奈感是非常强烈的。颔联“山势有情留古寺,海潮无意到孤洲”,“无意”“孤洲”等都显示出这种孤独和无奈。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有一天他来到了隆教寺,看到了出家人处变不惊的从容态度,不禁激发出强烈共鸣,引以为精神上的同道。尾联“自觉行踪犹廓落,五湖烟雨钓鱼舟”,简直就是内心向往的宣言了。这与他在《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中所表露的心迹是一样的。其一中的“渐觉浮生冗, 何劳来去踪”,其二中的“鹤梦来何处? 龙吟隔几重”,都清楚地表达了他如果抗清失败,就遁入空门的思想。
在舟山期间,张苍水几乎走遍了岛上的各个大寺,并多有诗作留念。一直到康熙二年,由于鲁王病死,张苍水解散了抗清义军,自己只带极少数随从,入孤岛隐居。张苍水终于有以平静之心来做“采薇吟”的机会了。对于他而言,这既是一种失败,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精神上的重新解放。他在《游隆教寺》所向往的“五湖烟雨钓鱼舟”,现在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只是清廷不容许他存在,他只好在西湖旁边高吟“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走向与山水自然告别的最后霞光。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