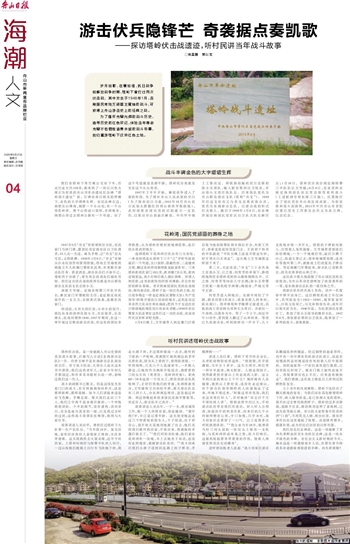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游击伏兵隐锋芒 奇袭据点奏凯歌
——探访塔岭伏击战遗迹,听村民讲当年战斗故事
吴以龙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05月21日 第 04 版 )


如今的塔岭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翁盈昌 吴以龙
岁月如歌,往事如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塔岭下曾打过两次伏击战,其中发生于1948年1月,击毙国民党地方顽匪王雪瑜的战斗,可称得上舟山游击史上的经典之战。
为了缅怀先辈光辉的战斗历史,追寻历史的红色印记,体验当年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战斗场景,我们重游塔岭下这块红色土地。
战斗丰碑金色的大字熠熠生辉
我们在塔岭下秀竹庵公交站下车,往北行走大约150米,就来到了一块以白色大理石为材质的舟山市革命遗址纪念碑“塔岭战斗遗址”前,石碑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金色的大字熠熠生辉。在纪念碑左边,鼎梁尖山峰南,隔着一个小山包,有一个山岙花岭湾。整个山岙成口袋形,坐西朝东,绕着山岙过去塔岭公路有一个弯道,出了这个弯道就是直路平路,塔岭伏击战就发生在这个小山岙里。
1947年下半年开始,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填补舟山人民武装的空白(为了保存抗日力量,1943年10月舟山抗日武装大都撤往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此时需要在国民党的后院建立一支队伍,以策应舟山的最后解放。中共华中海上工委决定,将镇海收编的抗日反蒋的徐小玉部队,编入浙东第四自卫纵队,并由徐小玉担任纵队长。后来纵队更名为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简称“舟支”)。1948年后这支队伍又与多支反蒋武装合并,更名为东海游击总队,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随后于1948年1月6日,在金塘洋面击毙国民党东区自卫队大队长顾任父;1月10日,塔岭伏击战击毙定海保警三中队队长王雪瑜;6月6日,在龙堂岭击毙定海刑侦队队长贺忠根等系列战斗(上述匪顽号称东海三只狼),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舟山的反动武装。为彰显塔岭战斗的胜利,2013年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以党史工作委员会名义为此立碑,以志纪念。
花岭湾:国民党顽匪的葬身之地
1947年5月“舟支”所部梁阿岳分队,在沈家门马峙门港,遭国民党定海东区自卫队围杀,43人无一生还。痛失手臂,让“舟支”忍无可忍,义愤填膺。1948年1月9日,“舟支”在塘头冷水坑宿营时获得情报,得知王雪瑜要到刚建立不久的螺门警察队巡查,布置剿灭游击队任务。获此消息,游击队员们兴奋不已。毒蛇终于出洞了,要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雪恨。担任这次伏击战的指挥员就是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的支队长徐小玉。
顽匪王雪瑜,定海县保警三中队中队长,兼沈家门军警联防主任,是定海反动武装中的一支主力,全副美式装备,盘踞在沈家门。
俗话说,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技巧。渔民出身的指挥员徐小玉,生在展茅,长在塘头,抗战时期和1946、1947年期间,在这一带开展过长期的游击活动,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认为塔岭有绝好的地理优势,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选择塔岭下花岭湾打伏击有三大好处,一来花岭湾是从塔岭下三个“之”字形弯道的最后一个弯道,呈口袋形,隐蔽性好。二是撤离方便,翻过花岭湾岗隔壁就是赵家岙村。三来塔岭距离沈家门10公里,距离螺门5公里,距离定海更远,战斗打响后敌人接应困难。所谓人和优势,这里的敌伪组织相对薄弱,并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老百姓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倾向游击队。塔岭下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抗日战争期这一带是定海东区警察大队(共产党领导)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这里还出过革命烈士吴由台和吴瑞成;把四个子女送往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抗日母亲吴杏娥;1940年东区警察大队还曾在这里打过一次伏击战,有成功歼灭汉奸林章财先例。
1月9日晚上,王雪瑜等人到达螺门后便召集当地的保警队和乡保长开会,布置工作后,准备连夜赶回沈家门去。王的部下姓邓的中队副说“中队长晚上还是不要走为妙,好歹明天白天再走”。这天晚上王雪瑜便这样留下来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舟支”三十余名战士在徐小玉、江之铭、何育芳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埋伏在塔岭花岭湾山脚两侧树丛中。江之铭、何育芳等10余人守北侧;徐小玉带警卫班配一挺机枪守西侧;梅耐青、芦瑞元等守正面。
何育芳进入阵地后,在路中间挖了个洞,洞里伏着3名战士,准备在敌人到来时,跃出洞口,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正面进攻,其他的战士伏在树丛里和石头背后。并派出一个岗哨,以落伞为号。等了一个上午,时近中午11时半,看到敌人翻过了山岭而来。等待已久的游击队,听到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十支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打得敌人鬼哭狼嚎。王雪瑜看着匪徒们纷纷倒地,一个一个地被打死,最后只剩下自己,知道大势已去,便举枪喊着投降,还没有等他叫第二声,就被战士们的复仇子弹击毙。等定海螺门军警赶来,游击队已高歌离去,消失在莽莽的山林之中。
这次战斗极大地震慑了舟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舟山革命史册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东海游击总队的一篇经典之作。
我游击队有四名战士负伤,其中一名腹部中弹不治身亡。这位牺牲的战士年仅26岁,名叫张友全(1922—1948),展茅张家村人,自幼父母双亡,与兄弟相依为命,成年后以做木匠为生。1946年底,为抗拒国民党抓壮丁,参加了徐小玉领导的锄奸大队。1947年6月,参加浙东第四自卫纵队,他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表现勇敢。
听村民讲述塔岭伏击战故事
塔岭伏击战,是一场能载入舟山史册的真实战斗故事,后被写入小说《东海游击总队》一书。作者王博平是东海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对于战斗信息,大部分人是从这本书中获得,我们这些老年人,在青少年时几乎都读过,和许多革命题材小说一样,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
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斗,在百姓脑海如同昨天,还是那样新鲜,那样震撼。如今人们讲起来还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那天我们走访三个人,他们之中两个是亲眼目睹的,一个听他奶奶讲的。个中的细节,没有虚构,没有旁白,完全是最为真实的一面,以及我过去听到过的,这些战斗故事实在难得,值得与大家分享。
故事讲述人吴由华,曾担任过塔岭下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当年我18岁,家无田地,家里经济靠给人家做雇工维持,生活非常困难。这天我挑担去大展卖柴,近中午时回家,上塔岭时刚好与保警中队的人同行,一过山岗他们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下岭,我走小路下岭,才过塔岭墩庙一点点,就听到下面的一声枪响,我就慌忙躲到路边的茅草丛看究竟,因为从上看到下,看得很清楚。一听到枪响,只见六个人迅速弃车,一齐跳入路边,以地坎作为掩体开枪还击,接着看到三问头方向(笔者注:花岭湾对面),距离60—70米远的一个坟头上,埋伏的游击队机枪响了,正好打到他们的背面,东西两面夹击,王雪瑜和卫兵纷纷中弹,那天游击队足有三四十人,分东西两边埋伏,还发起过冲锋。将近傍晚赶来很多国民党海军警察等,有近百人,游击队早已离开。”
故事讲述人吴昌年,一子一女,都在城里工作,他一个人休闲在家,很是健谈。“那年我7岁,早已是记事年龄。这天屋旁地边走过三个带着枪的陌生人,个子很高,出于好奇心,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跟了出去,他们见到我后就叫我回家,不要出来,我就躲到草蓬后面去了。”“我们村的吴松盛,他们家在花岭湾有一块地,早上去地里干农活,还没有走到地旁,就被游击队劝回。”“战斗结束后我们小孩子还到田边路上拾子弹壳、手榴弹柄……”
讲述人吴以善,塔岭下老年协会会长,从普陀动物防疫所退休。“我奶奶,名字张满姐,当年五十多岁。这天大清早,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烧火做饭。人刚走到园子,突然就看到对面山上有走动的人影。这么早到自家的柴山上干什么?她怀疑有人在偷柴,就到山上看究竟,还没有走近柴山,有个游击队领导模样的人快速地走了过来,叫她不要过来,‘阿婆这里有危险,我们在这里要打坏人’,并对她讲‘回去后千万不要向别人讲’。奶奶虽然年纪已大,平时游击队经常在我们村进出,好人坏人分得清,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回来后的几个小时始终憋在心里,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战斗结束后总算舒了一口气。以上是我多次听到奶奶讲的。”“我父亲当年28岁,他曾讲当时三问头前的一座坟头上架有一支机枪,与花岭湾形成夹角之势,战斗打响后,这挺机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敌人两面受到攻击无法藏身”。
还听到其他老人说起“战斗结束后游击队翻越花岭湾撤退,经过隔壁的赵家岙村,其中有一名中弹负伤的游击队战士,说是在收缴战利品时被还没有死的敌人打中腹部的,抬到赵家岙一户农民家里进行施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躺在门板上始终血流不止,用银番饼压也止不住,后来连夜被抬走”。我们猜测,这名战士就是以上讲到过的牺牲张友全。
七十余年的风雨兼程,塔岭下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站在高处瞭望塔岭下村,映入眼帘的是,是已容颜大变的塔岭,找不出过去曾经熟悉样子。塔岭经过多次降坡,道路平且直,路的两旁还种了景观树,已成为高等级公路。昔日的大家想象中的花岭湾“口袋”,不再荒无人烟,蛇虫出没。现在许多村民在这里建起了别墅,房屋排列整齐,错落有致,成为村民们宜居的自然村落。
我们驻足纪念碑前,这是一块凝聚了革命先辈鲜血甚至生命的纪念碑,这是一块永不褪色的丰碑,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今天,她永远是一块激励家乡人民,沿着先辈开辟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的丰碑。向先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