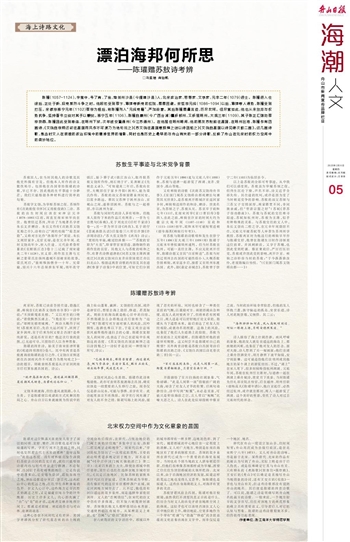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漂泊海邦何所思
——陈瓘赠苏敖诗考辨
冯坚培 肖怡帆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5年02月06日 第 05 版 )
□冯坚培 肖怡帆
陈瓘(1057~1124),字莹中,号了斋、了翁,南剑州沙县(今福建沙县)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元丰二年(1079)进士。陈瓘进入仕途后,正处于新、旧党激烈斗争之时。他起初受到蔡卞、章惇等新党的拉拢,屡屡回避。宋哲宗元祐(1086~1094)以后,章惇等人得势,陈瓘受到打压。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相后,将陈瓘列入“元祐党籍”,严加迫害。其后陈瓘屡遭流徙,历尽坎坷。但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放弃与权势抗争,坚持著书立说对其予以鞭挞。崇宁五年(1106),陈瓘自廉州(今广西合浦)量移郴州,又移居明州。大观三年(1109),其子陈正汇弹劾蔡京获罪,陈瓘因此受到牵连,在明州下狱,次年被安置通州(今江苏通州)。在他居住明州期间,他的朋友苏敖前往昌国,在明州出海,陈瓘作有四首诗:《文饶自京师还欲往昌国而风作不可渡乃为绝句戏之》《苏文饶往昌国意颇惮之送以诗因勉之》《文饶自昌国以诗见寄次韵二首》。这几首诗歌,是当时文人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的精神世界的缩影,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与舟山有关的一部分诗歌,反映了舟山在北宋时的权力空间中的微妙地位。
苏敖生平事迹与北宋党争背景
苏敖其人,在当时其他人的诗歌及其他史料偶有言及,但他本人所作的诗文散佚殆尽,包括他在昌国寄给陈瓘的诗歌,早已不存。因此他的生平事迹十分渺茫,我们只能根据各种材料进行简单的勾勒。
苏敖字文饶,为宰相苏颂之侄。苏颂作有《次韵敖侄书怀》《又用敖侄韵》二诗。苏敖的出生时间应该在宋神宗元丰(1078~1085)以前,而直至南宋初年尚在世。他曾经过苏州,拜访了当地著名学者朱长文并赠诗。朱长文作有《次韵苏文饶见贻之什》,诗称自己“闲钓松陵”“茹芝深隐”,又将对方比作“洛阳年少”贾谊。朱长文闲居家乡,无官无禄,是在元丰年间。此时文饶尚年少,初入仕途。元代俞希鲁所纂的《至顺镇江志》卷十二记载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宣义郎、将作监主簿马元颖之妻荣氏在扬州遇贼不屈被害的故事,荣氏死后,“旅殡维扬僧舍一十年。兄荣嶷,绍兴十六年总领淮东军赋,明年改守镇江,始卜葬于此(镇江汝山),取丹阳苏敖文饶所作传,刻石纳于圹。见龚颐正《先朝忠义录》。”可知建炎二年后,苏敖尚在世,大概居住于家乡丹阳(润州),能为荣氏作传。苏敖的叔父苏颂原籍泉州同安,以故乡路远,葬其父苏绅于润州汝山、京岘山之间,遂移居润州。苏敖与之一起移居,亦以润州为家。
苏敖与同时代的诗人多有唱和,但他本人留传下来的作品只有两首:一首为七言绝句《春晚》,见于刘克庄《后村千家诗》卷一;另一首为怀古诗《鸿沟》,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六所引许顗《许彦周诗话》:“苏大监文饶作《鸿沟》诗云:‘置俎均牢彘,峨冠信沐猴……’”苏敖的官职为“大监”,即掌管宫室营造、器物制作的将作监的长官。其他文人与苏敖的唱和之作,有著名诗僧道潜的《同苏文饶主簿西湖夜泛》《次韵文饶同自龙井出资国度泛舟以归北山》。根据这两首诗歌的内容及其在道潜《参寥子诗集》中的位置,可知它们分别作于元祐五年(1090)夏与元祐八年(1093)秋,苏敖与道潜一起游览了西湖、龙井、资国寺、孤山等地。
又有韩驹的诗歌《次韵苏文饶待舟书事》、《至国门闻苏文饶将出都戏赠长句兼简其兄世美》,是苏敖离开都城汴京返回家乡时,韩驹相送而作的和诗、赠诗。世美名京,为苏颂之子、苏敖从兄。苏京卒于政和七年(1117,见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卷四),在此之前,韩驹在汴京的时间大约为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至政和(1111~1118)初年,政和末年可能短暂还朝(据韦海英《韩驹行年考》)。
而苏敖与陈瓘的诗歌唱和发生在崇宁五年(1106)至大观三年(1109)间(陈瓘于元祐末年曾权摄明州通判,但当时苏敖在杭州,可能一直任主簿,不应无故离开任所,陈瓘诗题又言其“自京师还”,苏敖当时经过明州去昌国的可能性很小),大概苏敖告别韩驹,离京返乡后,接着又至明州东渡昌国。此外,据《嘉定赤城志》,苏敖曾于崇宁二年(1103)为仙居县令。
以上是苏敖的全部可考事迹,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敖虽为宰辅苏颂之侄,但终生沉沦下僚,声名不彰,诗文近乎全部失传。其仕途的坎坷,或许是因为受了当时朝廷党争的影响。苏敖的叔父苏颂与三苏父子交情深厚,两家籍贯不同,非同族亲戚,但“常讲宗盟之好”(苏轼《荐苏子容功德疏》)。苏敖与苏轼的交往难寻踪迹,苏轼知杭州时,苏敖为主簿,似乎有种特殊的关系。与苏敖交往的文人中,朱长文崇尚二程之学,在元丰年间隐居不仕,元祐元年被苏轼等人举荐为苏州州学教授。苏敖离京时为他送行的韩驹早年亦与陈瓘交好,他曾在陈瓘生日时作诗颂美这位前辈,并讽刺新法,又学于苏辙,也因此受到贬谪。蔡京秉政后,严厉打压旧党,苏敖或许因此受到影响,离开汴京。韩驹之诗形容当时的苏敖:“于今落落谁汝怜,老屋陈编自怡悦。”(《至国门闻苏文饶将出都……》)
陈瓘赠苏敖诗考辨
离京时,苏敖已决意告别仕途,隐逸江湖,韩驹在《次韵苏文饶待舟书事》一诗中说:“不须锦缆系吴樯。”又以对方的口吻说:“看我飘然五湖去。”(他在另一首诗中说:“却树吴樯背城阙。”两诗大概作于同时)苏敖离京后,先沿大运河而下,回到了家乡润州,至于后来为何又要去昌国?是单纯游览,还是另有目的?他这次行旅的意图,已无迹可寻,只留给后人以各种想象。
陈瓘的四首诗,始见于南宋张津所纂的《乾道四明图经》卷八。其中有两首是苏敖渡海前陈瓘的送行之作。《文饶自京师还欲往昌国而风作不可渡乃为绝句戏之》一诗的题目,明确表明苏敖是从汴京回到南方后打算东渡昌国的。诗云:
“欲冲高浪却沈吟,酒近瀛洲懒得斟。莫道颠风无好意,为君吹过远归心。”
文饶本欲渡海,但恰逢风波阻路,令人生畏,于是陈瓘便以戏谑的方式化解其愁闷之心。舟山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蓬莱、瀛洲。文饶前往昌国,或许是辞官后,想要去海上隐居、修道。若真如此,则前方的海岛就是他心目中的归宿,不然陈瓘怎么会将他这次行旅称为“远归”呢?陈瓘写对方面对骇人的风浪,沉吟惆怅,连酒也难以下肚,于是又戏言这场狂风能帮他传递归去的心愿。陈瓘在宽慰友人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在逆境中乐观豁达的态度。《苏文饶往昌国意颇惮之送以诗因勉之》一诗似乎是在同一种情境下所写,诗云:
“已闻舟楫具,那得苦留君。雨过霜风急,帆飞雪浪分。长途方策足,暇日正论文。功业他年事,风波岂足云。”
文饶对风浪心生畏惧,陈瓘作此诗来勉励他。此亦可表明苏敖渡海去昌国,确实应该是一段重要的人生修行之旅,而非仅仅是游山玩水,可能与事佛、求学有关。此诗起笔虽言不再挽留,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友人的不舍之情。颔联写海上的风浪,展现了恶劣的环境,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以激励对方。颈联语调由急转缓,说友人此时要离开了,但将来若有闲暇之日,两人还是可以好好地讨论文章的。陈瓘从当下遥想未来,最后表达了对友人历经艰险,成就功名的祝愿。这海上的风浪,也象征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险阻。苏敖当时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陈瓘仍对他的前途怀有期望,这又何尝不是陈瓘对自己的期望?另外两首诗歌是苏敖自昌国寄诗后陈瓘的次韵之诗。《文饶自昌国以诗见寄次韵二首》其一云:
“百川滚滚到来休,此是人间第一流。鲸鬣为君翻骇浪,兰苕空自满汀洲。”
开篇描绘了百川归海的壮阔景象,气势磅礴。“此是人间第一流”指眼前广阔的大海,暗含了对友人才华的称赞。后两句动静结合,诗中写到“鲸鬣”,未必是实景,可能只是形容海浪之巨,古人常以“鲸鲵”比喻大恶之人,诗人在此处似暗指朝中蔡京之流。当时政治环境非常险恶,但他的友人怀抱兰蕙,独守偏远的孤岛,安贫乐道,诗人对此既崇敬,又惋惜。其二云:
“海邦渺渺知何在,风入高帆顷刻过。何似一樽湖上酒,月明安稳照寒波。”
诗人描绘了海上壮阔浩渺,疾风呼啸的景象,他的友人就处在遥远的海岛上。那疾驰的风帆,也象征了他对友人的思念。面对大海,诗人想到了另一幅画面:他们在湖上乘舟饮酒赏月,明月静照下波平如镜,安宁而温馨。这可能是指他们在明州或其他地方的某个湖上的游览经历。不过,“湖上”在宋人笔下,很多时候特指杭州西湖。元祐年间,苏敖在杭州任主簿时,与道潜一起在西湖上乘舟赋诗,欣赏月下美景。当时陈瓘先任礼部贡院点检官,后在越州、明州任职(据杨高凡《陈瓘年谱》),他自京赴任,必然经过杭州,或许就在那时,两人一起游览了西湖。这个美好的剪影,寄托了诗人对过去元祐时代的怀念。
北宋权力空间中作为文化意象的昌国
陈瓘对这位飘荡天涯的友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宽慰、赞许,其诗歌也是对自身境遇的写照,字里行间不乏苦闷之情,同时也交织着古代士大夫的那种“处穷达如一”的豁达态度。没有材料能直接告诉我们苏敖去昌国的真实目的,我们只能根据诗歌内容与时代背景进行推测。不论如何,昌国似乎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传说中的蓬莱山,是安期生隐居、葛仙翁炼丹之地,神仙道教遗存丰富。在古代,远离政治中心的荒远之地,往往带有各种神秘的色彩。在文人心目中,这些地方是寄托愁苦的谪迁之所,又是躲避官场斗争的世外桃源。历史上许多文人,内心都充满了“出”与“处”的矛盾,这两者反映在地理空间上,那就是对都城、朝廷的眷恋与对山林、沧洲的流连。
这种心态在不同时代又有差异。美国学者谭凯分析了唐代墓志铭的出土地的空间分布后指出,在唐代,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的居住地“多集中于长安、洛阳二都及两京走廊地带”,而宋代以来,“帝国的权力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构,主要的政治精英更多地定居于地方,而不是京城”(《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第二章)。北宋以来的士大夫,即使在都城中担任要职,致仕后也往往选择在地方城市居住,尤其是江南地区。比如苏颂的家族本来世代居住在福建,后来苏颂成为宰相,没有像唐代的达官显宦那样落户京城,而是回到地方城市去了。只不过,他也没有回归遥远的故乡泉州,而是选择举家徙居润州。文人的“恋阙情结”,在宋代的诗文中仍有许多体现,但不如六朝隋唐时浓厚。苏颂像其他文人那样徙居山水秀丽、交通便利的江南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恋阙”与“隐居”的折中。
在六朝隋唐的文学话语中,都城以外的城市都带有一种乡野、边地的色彩。到了宋代,随着都城的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消解,文人对广大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有了更多的细致关注。苏颂的故乡泉州在唐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沿海贸易城市,当时也有个别当地的文人跻身朝廷任职,但他们很难像苏颂那样成为宰辅,清要之位往往为世居都城的大族所把持。北宋以来,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福建这样的荒远之地也变得人文荟萃,如陈瓘也是福建人。这些出身海裔的文人,对海洋有更多的关注。
苏敖冒着风浪去昌国,陈瓘对他百般鼓励,虽然我们不清楚其真正目的是什么,但结合当时文人的出处矛盾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这似乎也可以表明昌国在文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确切地说,它更多地作为一个带有“贬谪”与“隐逸”“修道”的含混意蕴的文化意象出现在文学中,而非仅仅是一个地区、地名。
唐代在舟山一度设立翁山县,但时间短暂;舟山再次成为县级行政区,是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文人对舟山的诗咏,亦是始于北宋。某些唐代、北宋的作品有的被认为写到了舟山,实际上则是出于后人伪托,或是很难确定它真与舟山有关。只有柳永的《煮海歌》《留客住·偶登眺》、王安石的《秃山》可以确定是直接写舟山当地情景的诗词,还有王安石的《收盐》一首也与舟山有关,但这些诗歌都没有提到舟山的地名。其后便是陈瓘的四首诗歌了。可以说,陈瓘之诗是明确写到舟山地名的最早的诗歌。一般来说,一个地方较早的文学书写,往往对该地方的典范形象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引导着后人对它的认知与想象。陈瓘的这些诗歌数量不多,但仍值得引起重视。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