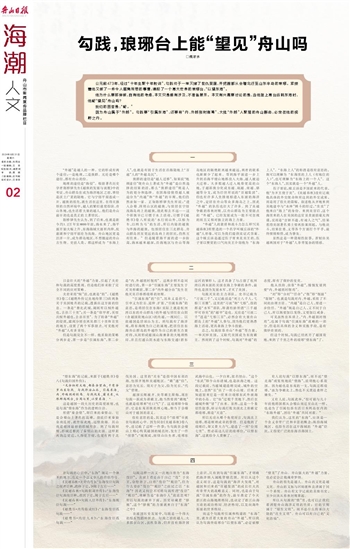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勾践,琅琊台上能“望见”舟山吗
倪浓水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4年08月31日 第 02 版 )
□倪浓水
公元前473年,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勾践终于一举灭掉了世仇吴国,并把首都从会稽北迁至山东半岛的琅琊。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建起了一个高大宏伟的琅琊台,“以望东海”。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自有他的考虑,本文只是稍有涉及,不准备展开。本文有兴趣要讨论的是,当他登上高台远眺东海时,他能“望见”舟山吗?
我们的回答是:“能。”
因为舟山属于“外越”。勾践要“引属东海”,还要将“内、外越别封削焉”,大批“外越”人聚居的舟山群岛,必定在他的视野之内。
一
“外越”是越人的一种。它的形成有两个途径:一是地理,二是族群。无论是哪个途径,都有舟山的份。
地理的途径是“海侵”。根据著名历史学者陈桥驿先生《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中的考证,舟山群岛在成为海洋地区之前,曾经是沃土广袤的陆地。它与宁绍平原连成一片。越族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越人的繁衍速度很快。舟山各地,也生活着大量的越人。他们是舟山最早的也是真正的土著居民。
陈桥驿先生认为,到了后来,也就是距今约1.2万年至8000年前,海水来了,海平面开始大幅上升,东海海域大面积内伸,杭嘉湖和宁绍平原沦为浅海。舟山地区更是汪洋一片,成为群岛地区。不想撤退的舟山古生物、史前人类,都这样成为“东海上人”,也就是有别于生活在沿海陆地上“百越”人的“外越岛民”。
族群的途径是“越人迁移”。如果说“地理途径”使舟山土著成为“外越”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的话,那么“族群途径”则是人为的划分和选择。在因海侵使得越人被迫分为“内越”和“外越”的早期,他们仍然亲如一家。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说:“进入会稽、四明山区的越族,与留居在宁绍浅海岛屿上的越族,彼此相去不远……这个部族早已习惯于水上活动,习惯于《越绝书》卷八所说的‘水行而山外,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所以内陆的越族与外海的越族,包括居住在三北群岛、舟山群岛甚至更远的岛屿上的居民,仍然互有往来。”但是随着海平面的进一步抬高,海床越来越深,沿海地区与舟山等海岛地区的隔绝距离越来越远,两者的联系也渐渐少了起来。等到海平面进一步上升到沿海平缓山地都没入大海,越人被迫大迁移,大多数越人迁入地势更高的山地,于越部族分化成东越、瓯越、南越、骆越等分支,成为后世所说的“百越集团”。但也有许多人坐排划船进入东面的海洋之中,定居在舟山等众多海岛之上,因此“外越”的队伍也壮大了许多。到了吴越争霸的春秋时期,以舟山群岛为主要据点的“外越”,已经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而且又相对独立的海上力量。
“外越”人的素质和战斗力怎么样?《吴越春秋》所塑造的一个名字叫椒丘诉的“外越”人形象,可以为我们提供实证式答案。这个椒丘诉是通过伍子胥来见吴王的,伍子胥以赞赏的口气向吴王介绍他为“东海上人”。“东海上人”的称谓是很有意思的,既可以理解为“东海里的上人(有地位的人)”,也可理解为“东海上的一个人”。这个“东海人”,其实就是一个“外越”人。
伍子胥说,椒丘诉是齐国派来的代表,他“为齐王使于吴”。《吴越春秋》没有记载他具体的外交使命和所达到的外交成果,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他从齐地来到吴地途中与“水神”搏斗的经过,“坐实”了他来自“海上”的身份。来到吴宫后,这个海里来的人在吴国的达官显贵面前毫无拘谨,反而是“言辞不逊,有凌人之气”,结果惹得吴国著名勇士要离拍案而起,与他决斗,结果在勇、义等各个方面打个平手,最终惺惺相惜,成为挚友。
显然这是一种隐秘性叙事,折射出吴越两国对于“外越”人非常复杂的情感。
二
日益壮大的“外越”力量,引起了夫差和勾践的高度重视。但是他们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
夫差采用“候”法,也就是“防”。《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的两条关于吴国地名的记载,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一条是“娄北武城,阖闾所以候外越也,去县三十里”;另一条是“宿甲者,吴宿兵候外越也,去县百里”。为了防备“外越”的侵扰,阖闾分别在离吴都三十里和百里的地方,设置了两个军事据点,可见他对“外越”人有多害怕。
但是勾践完全不一样。他采取的策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引属东海”,第二步是“内、外越别封削焉”。这两步棋不是同时进行的,第一步“引属东海”主要发生于灭吴称霸前,第二步“内外越分治”发生在他灭吴后移都琅琊的初期。
“引属东海”的“引”,其本义是拉弓,引申义为拉长、延伸、扩张,“引属东海”的意思,是将居住在东海(实际上就是杭州湾以东的舟山群岛)的外越与居住在山阴(含越国故地山区)的内越,一视同仁。以前越国是居深山为主,到勾践有了海洋观,将东海视为自己的属地,把居住在东海舟山群岛的外越作为自己的新生力量对待,从而形成越国山海兼备的大地理格局,并且打通山阴水道与东海交通(浙东运河的雏形),这才具备了与占据了杭州湾以西水面的吴国在海上争霸的条件,最终也是因为发展水军,才灭了吴国。
勾践灭吴的主力部队,史书记载为“习流二千”,又记载说是“死士八千人,弋船三百艘”。这里的“习流”和“弋船”,指的都是“水军”部队,即蒲松龄所谓“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越甲”是也。无论是“习流二千”还是“弋船三百”,必然会有大量舟山群岛上的“外越”人参与,因为他们更熟悉海上活动,更具备海上争斗技能。
总之,勾践依靠舟山“外越”等力量,一举灭掉吴国,又取代吴国成为东南霸主。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勾践对“外越”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他从扶持、依靠“外越”,慢慢发展到要“内、外越别封削焉”。
“封”即“分封”“任命”;“削”即“削弱”“限制”。也就是勾践对内、外越,采用了不同的治理方法。“内越”是自己人,要进一步信任。“外越”既是自己人,又不同于自己人,所以既要加以笼络,又要加以戒备。
可见虽然在本质上,“内、外越别封削焉”,也属于勾践“引属东海”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其具体的含义和实施手段,是有微妙差别的。
但这个时候,勾践已经离开了越国故地,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琅琊“望东海”了。
三
“望东海”的记载,来源于《越绝书》卷八《勾践归国外传》:
“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勾践徏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
这是越国一段大历史的高度浓缩,也是勾践“望东海”作为的逻辑自洽。
所谓“秦余望”,即后来的秦望山。它是会稽山上著名的高峰,据说后来秦始皇南巡时,就登临此地,远望南海。其山南是越国最初的都城所在。到了勾践时期,都城迁移到了秦望山的北面。这样距离海边更近,入海更方便,也更有利于北伐吴国。这里的“关东”是指中国东部沿海,包括齐地和吴越地区。“霸”通“伯”,意思为兄长。周天子为父,伯为兄长,“代父”管理。
越国长期被齐、吴等霸主欺侮,现在勾践一跃成为新霸主,他当然要到“霸地”也就是琅琊来“吐口气”了。这琅琊即今临沂,它是东夷部族的核心地,相当于会稽山对于越国的意义。
很有意思的是,其实这个“琅琊”早就在勾践的心中。因为同在《吴越春秋》卷八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勾践在会稽山上精心构筑越国的城邑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这个“东武”即今山东诸城,也是滨海之地。这段记载说,当越城建造刚完成,城外的空地上,忽然“长”出了一座小山坡。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一座来自琅琊东武外面海中的小岛。它“钻”过数千里地下,然后在越城外侧“冒”了出来。显然,这是一个象征性叙事,暗示勾践打败吴国北上称霸定都琅琊,都是“天意”。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勾践北上琅琊,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他到了琅琊后,却又费大力气,建造了一座“台周七里”、想必高达几层的琅琊台,“以望东海”,这就很令人费解了。
有人说勾践“以望东海”,而不说“望北海”或笼统地说“望海”,说明他心系故国。因为越也是东夷的一支,勾践迁都琅琊,“虽为争霸北上,然也不无重返桑梓之嫌矣。”
又有人说,勾践此举,“很可能与几十年前他将国都从会稽山南迁至山北一样,也是为了引属包括生活日本列岛在内的‘东海外越’,团结‘外越’共同对敌。”
我们认为,这里的“东海”,应该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和丰富的概念:既指海域地区,也指生活在这片海域的“外越”臣民,又指更广泛的东海沿海国土。
四
在勾践的心目中,“东海”既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价值符号。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东海役臣句践之使者臣种,敢修下吏,少闻于左右……”
《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东海役臣句践使臣种,敢因下吏,闻于左右……”
《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东海贱臣句践……”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东海役臣孤句践……”
《越绝书·内经九术》:“东海役臣孤句践……”
勾践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自称为“东海役臣”,表面上看是由于自己“役”于吴王,身份卑下,自称“役臣”“贱臣”,但为什么要在“役臣”“贱臣”之前冠之以 “东海”?因此又何尝不可将勾践所谓“役臣”“贱臣”,理解为是“东海仆人”的意思呢?所以勾践的谦卑下面,其实暗藏着“骄傲”,这个“骄傲”的力量就来自于“东海”之中!
在越国历史发展中,勾践是一个伟大的根本性的转折点。勾践之前的越人,大多都在山区,虽然靠海,但并没有海洋国土意识,只有到勾践“引属东海”,才明确把海洋纳入属地管辖范围,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是勾践的“海洋大发现”,对越国和后来的“百越集团”的成长壮大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是由于勾践“引属东海”的作为,最早奠定了今天浙江的山海地理格局,也决定了浙江山海互动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以及向海外拓展的世界格局。
而这个勾践所引属和构建的“东海”里,就生活着大量的舟山“外越”,所以我认为勾践登琅琊台“以望东海”,必定能够“望见”了舟山。舟山强大的“外越”力量,也必定会让他魂牵梦绕。
舟山的祖先是越人。舟山的文化是越文化。舟山的文脉与河姆渡和良渚属于同一个系统。舟山有文字记载的直接历史,至少应该从春秋时期算起。
所以从勾践的“望”里,也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舟山海洋文明的性质:它的早期属于“原生文明”,而不是什么传承自大陆的“次生文明”。舟山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