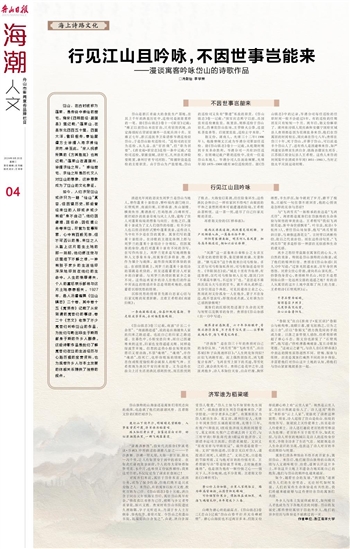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世事岂能来
——漫谈寓客吟咏岱山的诗歌作品
冼敏怡 李学辰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4年08月20日 第 04 版 )
□冼敏怡 李学辰
岱山,在古时被称为蓬莱,是传说中神仙的窑宅。南宋《四明图经·昌国县》里记载:“蓬莱山,在县东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耆旧相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仙灵药,尝至此。”宋人祝穆所撰的《方舆胜览》也有记载:“蓬莱山在昌国州,徐福求仙之所。”神仙窑宅、求仙之所是历代文人对岱山的想象,这种想象成为了岱山的文化象征。
如今,人们涉足岱山或许只为一睹“仙山”真容,但回望历史,那些曾经来岱的人却或多或少有些“身不由己”,他们因避难、因任命、因佐理公务等来岱。尽管为世事所累,心中有百般无奈,但不可否认的是,来岱之人从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注定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一种有别于家乡的生活烙印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生命中。人生的荣辱得失,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将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1927年,邑人汤濬编撰《岱山镇志》二十卷,其中卷十五《寓贤传》记载了从宋到清的寓客们的事迹,卷二十《艺文》收录了不少寓客们吟咏岱山的作品,为我们勾勒出非生于斯而献身于斯的外乡人群像。这些诗歌作品是我们了解寓客们在岱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的宝贵资料,也为观察外乡人与本土发展的休戚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点。
不因世事岂能来
岱山是浙江省最大的食盐生产基地,在其上千年的渔盐历史中,巡检司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据《岱山镇志》卷十一《职官》记载:“雍正以前岱山未设官治,只有驻防汎地,由定海镇标右营派驻额外一员配兵四十名。至雍正七年,浙江巡抚李卫奏请移岑港巡检驻岱山,于是岱山始有巡检司。”巡检司的长官为巡检,从九品,虽“官甚微”,但“职为甚要”。《清史稿·职官志》巡检一条中记载:“巡检司巡检,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隶州厅者专司河防。”缉捕奸盗是巡检的主要职责。由于岱山为产盐要地,岱山的巡检司又负有“警逻”私盐的职责。《岱山镇志》卷一记载:“按宝庆志熙宁以前,昌国监有巡检兼盐监。既置县,则移巡检于岱山驻扎,仍兼监岱山盐场,主管烟火公事,巡捉私茶盐香等。后别置监盐,巡检止守本职。”
陈文份,湖南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接替傅文江成为岑港分司第22任巡检。据《岱山镇志》卷十一记载,从乾隆时期到辛亥革命胜利,岑港分司一共有25任巡检。在明确记载户籍的巡检中,没有一位是岱山本地人。岑港分司人员流动频繁,光绪年间(1875~1908)就有10位巡检到任。据《岱山镇志》中的记录,岑港分司每任巡检的任职时间一般不会超过5年,有的巡检的任期甚至只有短短一个月。两年后,陈文份解职了。湖州南浔镇人周庆森和安徽宁国府宣城县人查禧都是因为佐理盐务来岱,他们在岱寓居的时间较长,周庆森在岱七八年;查禧在岱三十年,死于岱山,并葬于岱山,可以说是半个岱山人了。还有些人是因避难来岱,如严州遂安县增贡生洪自含、镇海县廪贡生刘芬、江苏镇江府金坛县人王希程。这些人来岱的时间集中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行见江山且吟咏
清道光年间的恩贡生刘梦兰是岱山当地人,曾作蓬莱十景组诗,赞吟境内蒲门晓日、石壁残照、南浦归帆、石桥春涨、鱼山蜃楼、横街鱼市、衢港渔灯、竹屿怒涛、白峰积雪、鹿栏晴沙的美景奇观与风土人情,建构了世人对蓬莱仙境的想象与向往。在他之后,蓬莱十景成为了文人们创作的母题。有不少诗人也以组诗的形式赞吟蓬莱美景,这些诗人当中有不少是在岱的寓客。寓客们写的蓬莱十景组诗,在诗歌的主题及体例上都与刘梦兰的蓬莱十景组诗十分相似,但因寓客的身份,他们对蓬莱十景有不同的书写。在写作内容上,刘梦兰更多是写地理物象和人文事象本身,而寓客们多将景、物、事作为媒介与载体,最终指向寓居体验的表达。在感情基调上,刘梦兰的蓬莱十景组诗的基调是欢快的,甚至还蕴蓄着诗人对家乡的自豪感。与刘梦兰热情讴歌家乡之景不同,这些远离家乡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并非总是明朗欢畅的,也蕴蓄着沉郁忧愁的情绪。
沉郁忧愁的情绪首先源自思家心切与归家无期的双重折磨。且看王希程的《南浦归帆》:
一条南浦路迢遥,恰喜归帆趁暮潮。等是绿波芳草地,去时偏惹客魂销。
《岱山镇志》卷三记载,南浦“计长二十余里”。“南浦路迢遥”,说的是出海捕鱼人家的归来之路迢遥,也说自己的归家之路迢遥。在暮色中,小船安恙归来,而自己因避难来到这里,归家也变得遥遥无期。同样是绿波芳草地,但想到这些小船在短暂的休憩后又要出海,不禁“魂销”。“魂销”,亦作“魂消”,指死亡,也形容极端的情绪,极度悲伤或极度愉悦都会减损人的精气神。王希程既为渔民平安归来而喜,又为这些在浪尖上讨生活的渔民感到担忧,而且担忧到了极点。大海变幻莫测,往往险象环生,这些渔民会和自己一样有家回不得吗?由眼前的平和之景想到将来可能遭遇的险境,王希程由喜转忧。这一喜一忧,道尽了自己归家无期的苦涩。
再看陈文份的《石桥春涨》:
镇西汊港夜通潮,雨润蘼芜绿到腰。万户炊烟堪入画,一篙春水恰平桥。
斜阳有客横鱼艇,明月何人奏凤箫。驷马高车驰道过,相如以后让谁骄。
“凤箫”这一意象来自秦穆公之女弄玉与萧史的爱情故事,象征婚姻美满,夫妻和谐。“驷马高车”这个典故来自司马相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时,司马相如还是穷书生。《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文份引用这个典故,可见其建功立业之心,然而此时文份孤身一人在他乡,妻子不在身边,他不禁哀叹:即使功成名就,又有谁为自己感到骄傲呢?
寓客们的沉郁忧愁还源于生命的无常与短暂以及飘零的身世。查禧在《岱山杂感(其一)》中写道:
梗萍身世感飘蓬,六十年华转眼中,寄傲应推浮海客,不才原号信天翁……往事都成鸿爪雪,倦飞那复忆西东。
“浮海客”是在岱三十年的查禧对自己的身份认知。“鸿爪雪”即“飞鸿雪爪”,出自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飞鸿在雪上留下的爪迹,等雪化之后,就会消失殆尽。查禧已是花甲之年,还流离他乡,诗人本如信天翁,自由烂漫,胸怀理想,半生浮沉,如今蹉跎了岁月,磨平了棱角,只能叹一句往事不堪回首,他的心情该是怎样的无奈与悲凉!
与“飞鸿雪爪”一脉相承的表达是“飞鸿爪印”,两者都是寓客们在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领悟的审美表达。王希程写“我似飞鸿留爪迹,客中身世感飘零”。叶尔良,杭县(今杭州)人,曾任岱山场知事,他写“鸿爪暂留斜日影,马蹄催送落花尘”。古时常以鸿雁传信,故以之代表音信。而在这些诗句里,“飞鸿爪印”更多是形容一种漂泊无依感和生命的虚无感。
离乡之愁经常盘踞在寓客们的心头,大自然的美景,特别是岱山独特的山海景,成了他们的精神归宿。查禧在《岱山杂感(其九)》中写道:“过客光阴逝水流,百年身世两悠悠。厌看尘世心劳拙,虔向名山顶礼优。”俗事伤身劳心,查禧朝拜名山,何尝不是想问仙山借一处远离尘嚣的逍遥之地?有的诗人从寓居的这片土地中汲取了向上的力量。王希程诗《石壁残照》云:
千寻石壁耸嵯峨,
留得苍茫夕照多。
几度登高凭远望,
壮心必奋鲁阳戈。
“鲁阳戈”出自《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后以“鲁阳戈”谓力挽危局的手段或力量。日落之景常使人感伤,但希程却燃起了雄心斗志。陈文份也游览了“石壁残照”,他写道:“休嗟薄暮崦嵫景,复旦诗歌振笔题。”这凌云之豪气,与诗人在《石桥春涨》中表达的惆怅哀怨迥然不同。舒畅、振奋与怅惘、沮丧是寓客们截然不同的异乡体验,丰富着他们对岱山这片土地的认知,将他们与岱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济军谁为稻粱嗟
岱山独特的山海景还是寓客们寄托志向的载体,也造就了他们的凛凛风骨。且看陈文份的《鹿栏晴沙》:
鹿栏山下饶平沙,明媚晴光望眼赊。入梦客曾蕉叶覆,济军谁为稻粱嗟。
珠玉灿烂黄云重,金雾迷茫白日斜。好似潇湘图画里,一群飞鸿落蒹葭。
“潇湘落雁图”,指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书画》中所描述的潇湘八景之一——平沙落雁。沙滩一望无垠,大海一碧万顷,阳光一泻千里,让人有如置身于画中的感觉。在如此壮丽的美景面前,个人的得失荣辱都如梦里花、水中月,也难怪文份猛然醒悟:我来这里任职,不仅仅是为了谋求衣食而已!
对寓客们来说,寓居于岱非本意,或因公务,或为了保全性命,但他们绝不是只求安饱之人。来岱后,有的寓客以振兴文教、教化百姓为己任。《岱山镇志》卷十五载,洪自含于同治元年航海至岱后,寓居岱山两年有余,“惟孜孜以劝善为己任,暇则与乡父老考求掌故,振兴文教。查宋时有岱山书院遗址久湮海隅,学子无所适从,乃谋于乡人士方炳泰、邬兆权等,募资兴复。今岱山之有蓬山书院,其端实由自含发之”,由此,洪自含深受岱人敬重,“岱人士知与不知皆称先生而不名”。镇海县廪贡生刘芬印避难来岱,“讲学授徒,一时学者多从之游”。有寓客甚至为岱人献出生命。莫文田,湖州归安人,光绪十年间来岱任五属商廒经理,光绪十三年,有板户(即盐民)因收盐洋钱兑换的问题受亏,莫文田私允板户之请减去四十文后,与三所甲商(即盐商代表)商议收盐洋价,又禀请丰运司卫抚部,但请求被驳,文田又“星夜至省与甲商抗议”,最终还是徒劳一场。文田“怏怏返甬,以食言无以对岱人,遂投甬江而死,人咸惜之”。文田之死,自是他的节操所致,又与他对百姓的怜悯有关。王希程能写出“等是绿波芳草地,去时偏惹客魂销”,也是因为他有一颗怜悯之心——悯天下人,不分地域,也不分贵贱。且看陈文份的《白峰积雪》:
磨心岭上白如银,云里人家绝俗尘。路为峰高皆曲折,山因雪积失嶙峋。
可怜铺絮怜寒士,惯把堆盐误细民。戏海飞鸿留爪印,丰年有兆卜三春。
白峰为磨心岭的最高点。《岱山镇志》卷二《志山》记载“岱山山势平衍并无奇峰峭壁”。磨心山海拔也不过两百多米,但陈文份却说磨心岭上有“云里人家”。既然是云里人家,住的自然就是仙人了。诗人还用“绝俗尘”来形容“云上人家”,更强化了读者这种联想。明显,诗人延续了岱山是仙山、仙境的传统书写。颔联说上天怜爱寒士,其实是诗人怜爱寒士。诗人还打趣说老百姓将雪堆误认为盐堆。老百姓不至于盐雪不分,如此比拟,与诗人所在的地域以及诗人的巡检身份有关,亦使全诗多了生活气息。尾联既是诗人生命意识的呈现,也表达了诗人对百姓丰收的期盼与祝愿。
寓客们因各种缘由不得不离开家乡,寓居岱山。来岱后,他们被岱山独特的山海风情与人文韵味吸引、治愈,逐渐认识这片乡土,并在这片土地上不遗余力地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与岱山的羁绊也越来越深。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别处”逐渐成为人们的生存常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们的某些生命体验是有共性的,我们将越来越能够与这些曾经在岱的寓客们共情。
外乡人与本土发展休戚相关,如何吸引人才也成为当下各地关注的问题。岱山的发展史,那些曾经寓居于岱的外乡人,他们的异乡经历与体验是不能跳过的一页。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