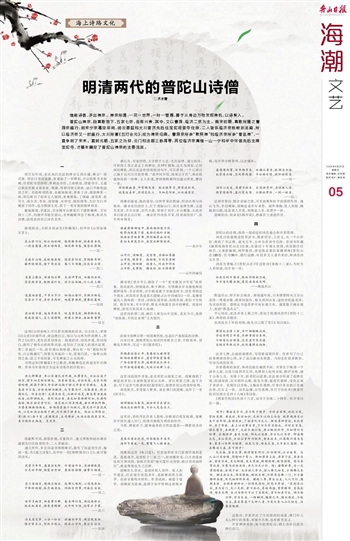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明清两代的普陀山诗僧
洪波雷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4年04月26日 第 05 版 )
□洪波雷
僧能诗者,多出禅宗。禅宗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善于从身边万物发现禅机,以诗契入。
普陀山禅宗,自真歇而下,五家七宗,各有兴衰,其中,又以曹洞、临济二宗为主。南宋初期,真歇所属之曹洞宗盛行;到宋宁宗嘉定年间,闲云德韶和大川普济先后任宝陀观音寺住持,二人皆系临济宗杨岐派法裔,所以临济宗又一时盛行,大川所著《五灯会元》,成为禅宗经典。曹洞宗所参“默照禅”和临济宗所参“看话禅”,一直争到了宋末。直到元朝,五家之沩仰、云门和法眼三脉凋零,两位临济宗高僧一山一宁和孚中怀信先后主席宝陀寺,才基本奠定了普陀山禅宗的主要流派。
一
明万历年间,在北宋后沉寂的律宗又得兴盛,禅宗一度式微。而在白华山南麓,却建起了一座禅院,开山祖师昱光如曜,任普陀寺住持时,曾刺血书经,上疏朝廷,请建寺宇,又逊让朝廷所赐金紫袈裟。期满,得都司梁文捐助,造白华庵做退居之所。其徒朗彻性珠、孙履端海观,皆善于诗,推崇禅茶一味,所以吸引了很多文人儒将,来庵雅集,丁继嗣、袁茂英、张可大、杨大名、李耘、徐如翰、吴钟峦、陆祖修等,先后为白华庵留下诗作,也为佛国文化,留下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
履端海观,字莲区,后在梅岑山磐陀石下建林樾庵。万历四十二年,内阁中书陆宝游山,在林樾庵拜会了海观,称其为诗僧,说明此时其已诗名在外。
海观的诗,大部分收录在《林樾集》,其中有《山居杂咏五首》:
是山俱可往,何必向崆峒。倦倚梅岑树,闲看涛弄风。
一径通篱落,两石峙西东。偶然捧书卷,随意就荫桐。
——其一
支遁买山隐,我欲蹑其踪。因思普陀近,常闻聒耳钟。
槛外饶绿筠,墙下有流淙。柴门不须掩,依仗白云封。
——其二
清晨上磐石,观兹旭日晖。光丽冲霄汉,水激向石矶。
霏霏雨雪来,飘飘湿纻衣。径尔还林樾,行人道上稀。
——其三
凌虚向赤霞,千步亦多沙。细韵山寮竹,长飘水碓花。
空濛云下宿,清冷月西斜。响屐曾谁到,萧萧说暮鸦。
——其四
夜分犹不寐,起来步林月。叹息劳生扰,顾影惭白发。
寒威侵逼人,觅火烧榾柮。烘罢上禅床,挺挺脊梁骨。
——其五
这组《山居杂咏》,可以看出海观的诗风。自古诗人,皆爱以《山居》命题作诗,而远绝红尘,每日与山林为伴的僧人,所作之《山居》,更有其真切体会。海观的诗,诗风冲淡,用词浅白,描写了梅岑山的四季风景,也写出了出家人的清冷寂寞。第二首最后一句,很有寒山的味道,寒山有一句“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而第五首最后一句,更如白话,一如寒山拾得之流,读之不觉枯索,可见禅家之心无挂碍。
可惜这本《林樾集》今已散佚,林樾庵也在清道光年后倾颓。所幸当年张煌言为这本诗集作的序犹存:
世之辟佛者,率以浮屠氏为外教,而瞿雲氏,亦往往逃于枯空,谓不如是则非禅也。然东林慧远,白社风高,未尝不陶情吟啸,则诡于禅之外非禅而拘于禅之中者亦非禅也。夫善易者不言易,今使进禅而赋诗,而字摹贝叶,句勒昙花,则亦偈而已。何名为诗?夫诗本性灵,而禅亦性灵,要自有活泼泼地者,此即禅机也。普陀端公者,吾未知其禅理何如,而微吟高咏,绝非枯空者可比。彼岂欲以诗名鸣哉,毋亦禅机所触,不禁其洒洒扬扬矣。余偶得其数十而讽之,固无贝叶昙花风味,以是知端公能超于禅,而不拘于禅者也。端公之师朗公,有《秋兴》数十首,清微宛淡,业奇厥世,而端公能续其宗风,真不愧传衣钵矣。是为序。
二
清康熙年间,海禁初弛,百废待兴。通元照机和徒孙潮音通旭先后住持普陀寺,二人皆能诗。
通元所作,多在其退居栴檀庵后,描写了其退居生活,编成一集,名《通元诗集》,其中有一组《栴檀精舍口占》,或可窥其诗风:
风景只年年,盈盈白发鲜。竹窗遥听水,清沼懒载莲。
日月闲中掷,烟霞世外妍。罢琴维绣佛,诸事不相便。
——其一
芝兰香满室,晴雨总相宜。地僻人难到,心闲鸟共知。
千峰环短榻,孤月映清池。问衲今何事,呼猿足自怡。
——其二
世外多幽赏,林泉事不群。春来啼旧鸟,雨过起新云。
玩水知鱼乐,闻香爱蝶醺。此中何不悟,指掌示于君。
——其三
浮生原是梦,六合一松关。识破水中月,观空镜里颜。
随方皆乐土,何地不深山。趺坐山穷处,看云自往还。
——其四
愚以为,对景抒情,五言胜于七言,尤其是律。通元的诗,可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禅诗。其17岁剃染,近九旬而寂,已经深悟禅机,所以在这些恬淡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一个已将自己融于山川日月的老僧。“此中何不悟,指掌示于君”,典出俱胝和尚的一指禅。文人朱谨,曾到栴檀庵拜访通元照机,赠诗一首:
深林藏幽屋,中有鹤发翁。枕石抱萝月,弹琴流松风。
寂寞运真宰,燕闲忘化工。不知是何世,云水满清空。
而潮音通旭,他的徒孙,自然常承其教诲,但诗风却与其相异。潮音在住持任上,忙于重振山门,再次易律为禅,又造先觉堂,不分宗派,历代大德,皆奉于其中,全山庵蓬,从此亦多以临济正宗自称 。潮音所作诗虽不多,但却流传甚广,其中列举两首:
谁裁蜀锦掷庭中,霜雨频经愈不同。
瘦影尚欺篱下菊,朱颜还傲岭头枫。
低垂会学娱亲舞,潦倒偏资益壮功。
更似未衰花月兴,夜深沉醉倚秋风。
——老少年
山中行,闲踏青。没意智,沿路扯葛藤
山中住,煨紫芋。拾枯柴,不伐长青树
山中坐,偶回顾。牧童儿,问我牛何处
山中卧,无事做。醒来时,红日将西堕
——山中四威仪
潮音的《老少年》,描绘了一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形象。用词浓烈,情绪高昂,殊于禅诗。可惜潮音并未像他师祖那样高寿,半百而殁,次年朝廷就下旨赦造两寺,没有等到这个消息,对其而言真是莫大遗憾;《山中四威仪》一诗,是潮音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诗,诗体似谣非谣,似偈非偈,类似于竹枝词。数百年来,不少学者,都在寻找蕴含其中的禅机。而是何禅机,恐怕只有其本人知晓。
这首诗的第二段,被后人奉为山中仪轨。直至今日,犹将“拾枯柴,不伐长青树”立为禁约。
三
法雨寺的禅宗第一祖别庵性统,也是位产量很高的诗僧。
自宋以来,题咏普陀山的诗作有数百之多,不胜枚举。别庵也不例外,写过一首《题普陀》:
熙潮鼎运海云开,朱履欣从破绿苔。
断彻旌旗横丽日,虚堂钟鼓震春雷。
广传衣钵贤王泽,遥溯源流大帅才。
伫听金鸡清报晓,九垓应效舞三台。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在普陀山展复之初。别庵接到了朝廷的圣旨:全面修复普陀山丛林。所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写下这首气势雄浑的《题普陀》,展望普陀山的美好前程。
春花秋月,多受骚人赞美。身在佛门的别庵,也作了一首《牡丹》:
谁将脂粉与春风,漏泄许多在碧丛。
雨洗淡红烟作幕,不令人见态还工。
这首诗,将牡丹比作美人脂粉,在烟雨后愈发妩媚。别庵并不因为遁入空门,而排斥被视为艳俗的牡丹。
当然,释家弟子,题咏最多的自然是莲花---佛教的圣洁之花:
羡渠水质出淤泥,衬绿凝妆万朵齐。
海印乍看成一色,鹭鸶飞入暗香迷。
别庵的这首《咏白莲》,写的是普济寺门前海印池的莲花。莲池夜月,是普陀十二景之一,而别庵所见,白天的莲池也有万种风情。如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连鹭鸶也为之沉醉。
别庵有几首诗,是感怀故人而作。故人扣平超直,任法雨寺监院多年,是别庵的得力助手。在南京募构木材时,积劳成疾,病逝于途中。别庵深为哀痛,造塔于扣平焚修过的观音洞,每岁率寺僧祭拜,以诗缅怀:
着履缘何事,穷年踏雪来。双梅从昔老,孤塔自今培。
乱草连云暗,悲风带雨摧。平公面目隐,挽仰动深哀。
——其一
泪尽心灰矣,思君不欲来。台花新雪衬,石径故人培。
朝赏债谁侍,暮行有鸟催。云根冰骨冷,一到一回哀。
——其二
这两首祭诗,饱含哀恸之情,可见别庵和扣平的感情笃厚。漫山飞雪,羊径崎岖,别庵还是年年来祭。洞外寒梅,故人所植,蜿蜒的山路,也是故人开筑,而物是人非,化塔中一抔。
别庵的诗,收录在《梅岑集》,慈溪名士裘琏作序。
四
普陀山的诗僧,值得一提的还有鸿昆能仑和开霁得辉。
鸿昆自幼就被送到普济寺,勤奋好学,工诗文,从一个小沙弥,做到了书记僧。道光五年,公举为普济寺住持。普济寺所藏《康熙南海普陀山志》志板,在嘉庆十年被火焚毁,鸿昆继任住持后,又重新编辑,网罗散佚,请定海县幕宾秦耀曾刻《普陀山志》20卷。住寺30年,德行远播,有很多文人慕名来访,和鸿昆诗文互答。
鸿昆为重编之《普陀山志》写过组诗《南海十二景》,当时为人所称道,其中有一首:
如来无刹不留名,胜地何殊舍卫城。
今日海天瞻法相,莲花朵朵放光明。
——佛选名山
佛选名山,即不肯去观音。唐咸通年间,日本僧慧锷从五台山求得一尊观音像,欲带回国内。船从明州出发,途经普陀莲花洋,为风浪所阻。慧锷认为是菩萨不肯东渡日本,遂置像于潮音洞上,故谓“佛选名山”。
平心而论,此诗并非上乘之作,类似于祝德风所作《普陀十二景》,典型的命题诗。
在鸿昆五十岁的时候,他为自己做了首《五旬自叙》:
蒲团也自惜三余,贝叶频翻略注疏。
学道须明言外意,参禅曾读古来书。
不难易处分难易,没实虚中见实虚。
自愧百年斯过半,依然魔障未尚除。
这首七律,比起前面那首,写得要高明许多。作者写了自己的参禅感悟和心得,末了还自谦尚未参透。当时也有很多僧俗,写诗为鸿昆祝寿。
开霁德辉的身世,和鸿昆能仑截然不同。开霁生于晚清一个读书人家,自幼习读四书五经,光绪初入杭州余杭、桐庐县衙,属于公务人员。光绪十年,到普陀山进香,在法雨寺拜谒了高僧化闻,而感宿因,次年到伴山庵,削发为僧,剔度名源辉,受具足戒于普济寺。化闻付以衣钵,又赐法名德辉,开霁后来在浙江各地丛林,任方丈一职。诗名远播,自号孤峰,刊行于世的有《僧家竹枝词》《西方乐四十八咏》等诗集。
《僧家竹枝词》共四十八首,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有开霁自序一篇:
嗟乎!佛法至今日,其不绝于缕乎。古时出家难,试经方度,官给度牒。秉戒后,参访知识,无刻不以向上为念。故晋魏唐宋以来千余年间,高僧辈出,了悟者代不乏人。朝廷尊师重道,优礼有加,异于常数。盖上以此事为重,下亦不肯自轻也。今时出家易,僧众愈多,真衲愈少,无论乡曲小庙,除应酬经忏外,不知修行为何事。宗教律净,杳为不闻。师无以为教,弟亦无以为学。即通都大邑,名山巨刹,亦往往重外而轻内,舍本逐末,以集缘兴造为急务,置身心性命为缓固。拈花之旨,西来之意,大半束之高阁。欲求佛道之盛,其可得乎?
戊戌春,昼长无事,偶将僧家所行,衍为俚词,以示徒辈。自入山以至舍报,得题四十有八。俾知若者上品,若者下流,若者当法,若者当戒,生大惭愧,发大勇猛,树精进幢,被坚固铠。思与圣贤比肩,不屑与流俗为伍,庶几不无小补。噫!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无非欲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方畅佛之本怀。顾末世众生,障深根钝,顿悟为难,计惟有念佛一门,十方诸佛所共讃,历代祖师所共劝。横超三界,带业往生,人人可行,圆顿直捷。永明寿禅师曰:“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是到家以后,直与宗门,无二无别。若不出此,东钻西搕,盲修瞎炼。贡高我慢,增长无明。自以为修行可以了生脱死,吾不知其可也。倘不悟正修,作为无益。一转瞬间,报缘已尽,随业漂流,不能自主,甚至袈裟下失却人身,不更大负入山之初志。汝曹其勉旃。
这篇序,开霁抨击了当时因时局动荡,佛门中人无心修行的现象,对现今丛林,也有教育意义。
开霁禅净双修,如今的普陀山,僧人亦多以此为修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