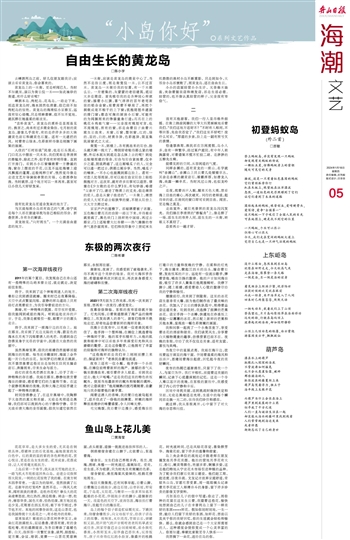- 放大
- 缩小
- 默认
自由生长的黄龙岛
陈小字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4年01月18日 第 05 版 )
□陈小字
去嵊泗列岛之前,好几位朋友跟我讲:应该去看看黄龙岛,你会喜欢的。
黄龙岛上的一米街,更是听闻已久。当时不知就里,误以为街长仅一米——如此袖珍的街道,有什么好看呢?
嵊泗本岛、枸杞岛、花鸟岛,一路走下来,抵达黄龙岛时,海水固然也清澈,但已经不如枸杞岛的惊艳。黄龙岛的海湾似小家碧玉,远没有惊心动魄,只是明眸善睐,但不知不觉地,就沉醉在她温柔的眼波里。
“古朴黄龙”,黄龙岛的质朴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尚未有过多商业染指。七月初的黄龙岛,游客几乎没有,有的是许许多多的大块赭黄色岩石和赭黄色石屋,还有一无遮拦的风。衬着青山绿水,色彩新鲜得像是刚摘下画架的油画。
入住的“石村船说”民宿,也是石头筑成,门口花丛中摆放一只木船,我们笑称是李清照的舴艋舟,除此之外,似乎没有鲜明印象。直到打开房门,看到小小石窗镶嵌着一方静谧的海,窗台上摆放的干花,以及不远处海塘上迎风飘摇的蓬蒿,这般纯粹空旷,恍然觉得像是走进文艺片导演侯孝贤的片场,心思澄净如洗。当时就想,这个地方可以一来再来,甚至可以小住几天好好发呆。
一
没有比黄龙岛更适合发呆的地方了。
与其说每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气质,毋宁说是每个人都在旅途寻找与自己相似的部分。折叠世界,各有各的解读。
黄龙初见,“向野而生”,一个充满自由意志的地方。
一米街,应该是黄龙岛的商业中心了,当然不是指长度,而是街宽仅一米,长不过百米。黄龙岛一米街给我的惊喜,有一千米那么长。一片密集的、灰蒙蒙的老旧建筑,底层大多是商店。首先吸引我的是各种随心所欲的窗:插着小红旗,喜气洋洋的百年老宅新装的铝合金窗;用着用着不够用了,再挖个洞做成毫不相干的上下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排门窗;憨态可掬的厨房小石窗,可能有的为闻腥而来的馋猫量身打造;高高在上的桃花斗鸡眼气窗……完全没有规划可言,也不用规划,所有的窗,都是由着日子由着兴致生长出来。木窗、石窗、塑钢窗,红的、绿的、蓝的、白的,材质各异,色彩迥异,简直集民居窗式之大成。
街宽一米,到楼上,各有挑出来的阳台,抬头就只剩一线天了。特别好奇贴得那么紧的墙壁,外层水泥灰到底是怎么抹上去的呢?到处是贴墙而建的邻舍,阳台与阳台紧挨着,仅半步之遥,别说跨越了,这边厢嗑瓜子的人,完全可以递一把过去,供那边厢分享。当然,嗑瓜子的唾沫,一不小心也能溅到那边脸上。若有一对恋人比邻而居,尽可以站在自家阳台上轻松拥抱对方。这次第,就有许多故事可以遐想。缪塞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一米街上,理想的爱人大可不必去钻狭窄的窗,不妨从阳台上大大方方跨过来。
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晾晒着被子衣服,五色梅沿着高高的台阶一路长下来,开得眼看就要疯了,黑色铁门上挂鲜艳中国结,再过去那家,门上还贴着大红春联……热气腾腾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它们和我印象中上世纪末生机勃勃的渔村小岛不断重影,只是到如今,大部分小岛都衰败了,而黄龙岛,还在自由生长。
小小的店面经营小小生计,无非柴米油盐,夹杂着服装店和理发店,都是生活必需。经营的,也不像认真经营的样子,完全没有市侩气。
二
没有其他游客,我们一行人显得格外招摇。在街上纳凉闲聊的大爷大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这地方还好不?”不时有人相问,不等回答,先自我否定了,“我们这里不好吧?没什么可看。”厚道的乡亲,脸上是一副有所亏欠的表情。
恰逢禁渔期,渔民都在悠闲度假,岛小人多,自有一种繁华,路过某户庭院,有中年人袒胸露背,对着谱架不慌不忙拉二胡。是胖胖的五柳先生啊。
捉襟见肘的空间,从容闲适的气度。
同样赤膊的,还有黄龙的一座山,名字就叫“赤膊山”。赤膊山上只长着几处矮矮草丛,其余是赤裸的赭黄岩石,雄霸浑厚,如潜龙入海,尚露一鳞半爪。当时风过山岗,也似龙吟之声。
是夜,枕着涛声入眠,醒来天色大亮,想看海上日出的雄心,再次破灭。同行的老师说,起得早的话,在房间的窗口即可看到日出。闻言,更是悔之莫及。
走出室外,被阳光普照的黄龙岛闪闪发光。我们躺在李清照的“舴艋舟”上,像是醉了一场,活生生的市井人间,活生生的一米街,转眼又不真切了。
总要再去一趟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