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
- 缩小
- 默认
海洋诗:多元视角与诗性海洋
——“海洋书写与个性表达”《厉敏诗选》研讨会纪要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4年01月08日 第 02 版 )

研讨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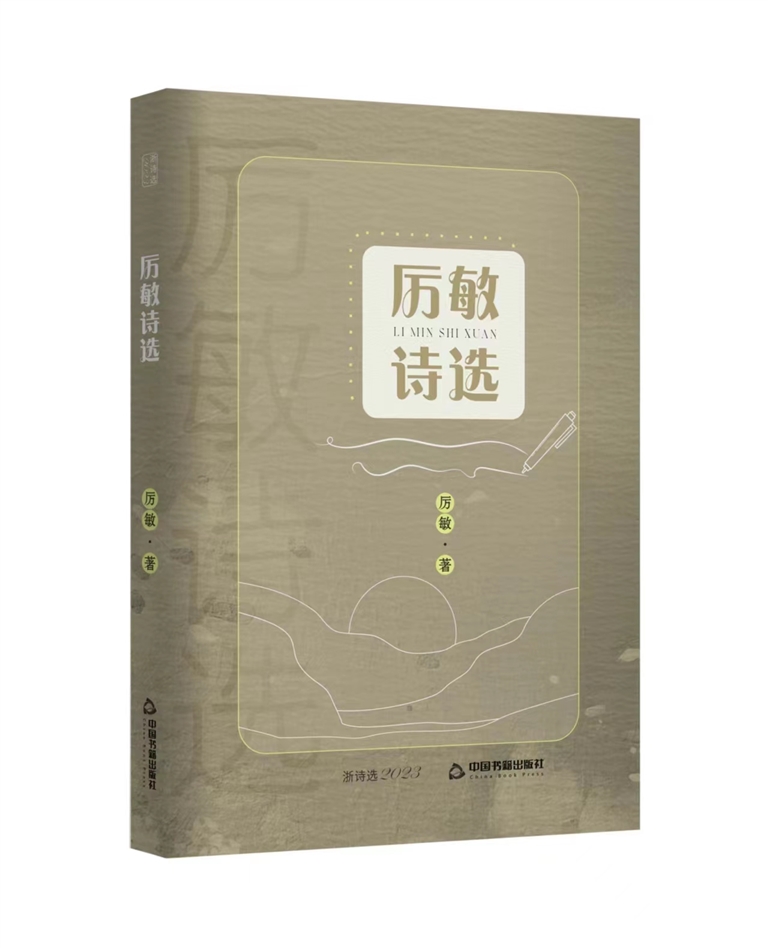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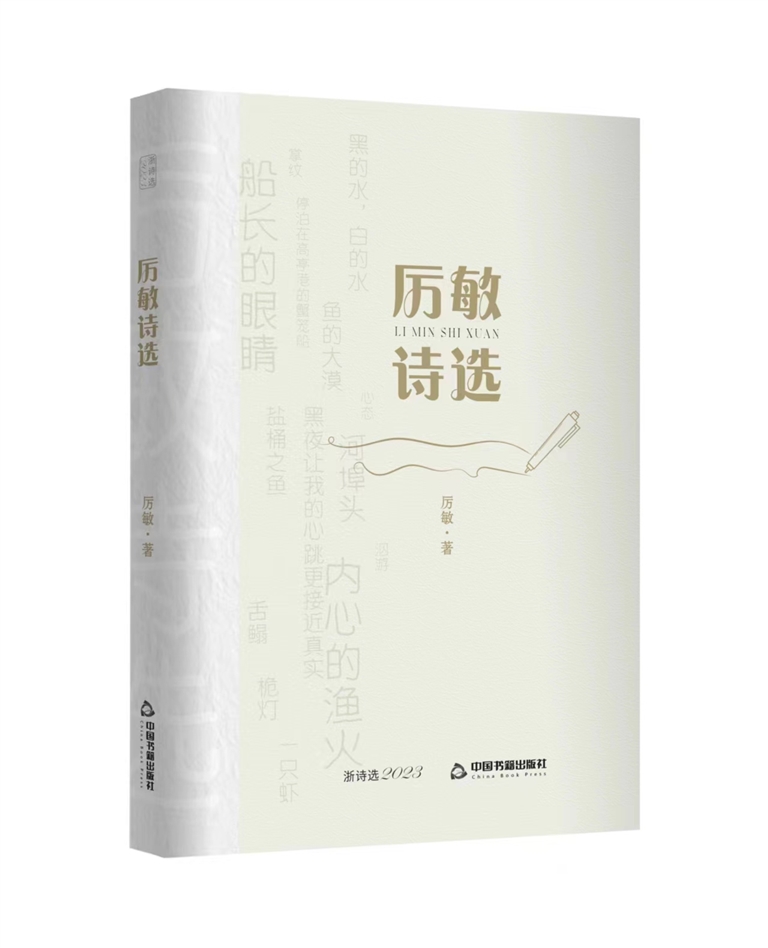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23年12月3日,由舟山市作协、岱山县作协联合举办的“海洋书写与个性表达”——《厉敏诗选》研讨会在岱山安澜阁举行。诗集《厉敏诗选》2023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该诗集以先后出版的四部诗集为序,精选125首诗歌编辑而成。厉敏是舟山海洋诗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厉敏诗选》从历时性视野客观地回溯了舟山海域的人文历史,从共时性视野全面地呈现舟山海域的时代内涵,从价值意蕴角度深刻洞察海洋文化独特的精神传统,具有较强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来自全市的15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围绕厉敏诗歌三十多年来在创作内容、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一、地域意识与海洋书写
白马(中国作协会员、市作协主席):厉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拿笔开始诗歌创作,不久即在全国各级报刊纷纷亮相。他的诗入选过我国那个时期重要的海洋诗文本《蔚蓝色视角——东海诗群诗选》,入选《浙江诗典》《浙江诗歌十年精选》《潮水奏鸣曲》《海边文丛》等诗选集。《浙江文坛》的年度诗歌述评,多次对舟山诗人厉敏诗作作了评点,李越教授的论著《存在的诗性敞开——新时期浙江海洋诗论》中,对厉敏的诗也作了专门论述。
我认为,厉敏的诗作有自己明显特征,他的诗作语言讲究节制,又不失现代品性。诗集《穿越动荡的午夜》中的《渔夫与海》《凄凉之屋》《蓝色之旅》《情感之盐》这几辑均是以海山岛情为内容的。海是厉敏诗歌的重心和总主题,他的诗以海岛风物风情风景的描写反映海岛生活,并寄以象征意义,作品《梭子蟹》等表现了渔夫人与自然交融的人性美、生活美、奋斗美。同时,“海岛意识”是他海洋诗的核心旋律,以多视角、多层面、跨时空表现海岛的风情、地理、历史、景物等海岛自然人文内容,并渗透对海洋、海岛、渔民的生活、生存、精神等方面的思考。
姚碧波(中国作协会员):我们每天生活在群岛之上,推门见山海,这个有着浓郁海洋文化底蕴的波浪家园,注定成为我们众多舟山诗人创作的根。厉敏作为群岛诗群的代表性诗人之一,海洋题材无疑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厉敏诗选》,就能让人感受到这种满满的海味,海洋诗所占比例超过六成。这本诗集,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海洋题材的广泛性,意象的繁杂,以及对拓展诗意所作出的探索。
厉敏从1984年开始诗歌创作,至今近40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守诗歌高地,埋头创作,辛勤耕耘,为我们奉献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体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对诗歌创作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总体看,他的创作是稳健的,无论早期、中期、还是近年的,诗歌都比较短小、精致,注重对语言的提炼和意像的塑造,富有内涵和张力。
许成国(市作协副主席):无论是海潮还是岛屿,如果说,早先的书写多为外部的观察与描述,那么后来的笔触则更多聚焦于时代的故事与变异,以及社会心境下的形象观照。时间美学的存在,不仅仅是四本诗集出版时间的先后,更是诗人对现实及书写的印痕,是诗人自己对不同岁月的一种心灵投射。
显然,厉敏的诗歌不是简单地“回归”海洋,他的“诗歌自觉”是从所描述、观照的不同时代来展现的。他以自己富有特点的诗歌语言与审美,沟通着海洋变革和社会变异中往昔与当下的联系,从中勾画出诗歌的历史维度,即时间维度;展现出诗人眼中海洋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即主体性维度。而蕴含在诗歌内核中的价值,更彰示着其海洋诗的价值意蕴和审美功能,即价值维度——这三者共同形塑了厉敏海洋诗的三维审美的立体风景。
李慧慧(省作协会员):这本诗选集中的诗,透过文字描绘出海洋的生命力和神秘感,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海洋的无限魅力。他写《鳗》在“风尘中长大”,可以“磨砺成一道道黑色的闪电”,赋予“鳗”以灵魂;写《乌贼》,把它比喻成伪装猎手,没有骨头,但藏有匕首。在《招潮蟹》里,又把招潮蟹比喻成夸张的兵器。这样的描写不仅让人感受到诗人的温暖情怀,更将海洋中的生物赋予了情感和思想,让读者体会到海洋生物的强大生命力。
《漩涡的方向》一诗,厉敏老师将漩涡比作卷笔刀,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人一种撕裂的感觉。他将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转化为“深不可测”的场景。厉敏老师眼中的大海,并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大海,而是他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这其中既有自然景观的形态,也有内在的精神象征。
谷频(中国作协会员、岱山作协主席):这么多年,他的创作延续了曾经的诗风,但也有许多创新与变化,他不断在寻找新的思想之源,避开了年轻时候写作的激情外露,更多地将智性、内省融入到字里行间,使他的作品多了一种厚重感,有时还带有一些神秘感。在他的诗中,我们读到的是诗化的现实、灵魂的现实,是逝去的过往、未知的未来。尤为可贵的是,他的诗歌语言淡然却富有张力,在意象的并置间呈现出的是非常具有动态感的画面,在诗歌体式的把控上张弛有度。
这部自选集,细读文本,字里行间不断生发出的鱼腥味,如海藻一样缠绕着诗人的肉体和灵魂。可以说,大海是他无尽的写作资源,这种资源不但是题材上的,更是情感上的。海岛独特的人文环境,诗人打捞的日常琐碎和生命况味都是其思想的深度漫步。独特的诗歌语境构成了舟山海洋诗歌创作的崭新一隅,亦有极具特殊地理精神价值的诗学研究意义。
二、多元视角与个性表达
孙和军(市作协副主席):我们的社会现实中有很多非此即彼,走极端甚至偏颇得令人无语的举措和认知,而厉敏的诗善于到达中庸境界。
第一辑《垂钓》这首诗既是在钓鱼,也是在钓自己的内心。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内心与鱼,与大自然形成一种关照。你是钓者,也是被钓者。你是钩,也是饵。《面对浩瀚,我替花鸟的名字担心》一诗写花鸟岛,一个诗意却弱不禁风的名字,独自渺小、孤独地偏离在海岸的边缘,独自对抗浩瀚的狂风巨浪,作者为这种以小搏大的悲惨不测,担心。第二首《花鸟的名字,是对太平洋的一种戏谑》,如果说第一首,花鸟是被动的,受欺凌和冷落的,第二首花鸟则是主动的,秉持傲骨的那种。柔弱的女子,独自面对外星球的洪荒;纤细的兰花手,阻止沧海桑田。勇气和胆魄成就了花鸟岛的傲骨。
王幼海(省作协会员):在诗选中,我们看到诗人视角的变化,这是一种创作过程中的主体自觉性的转变,一种努力想从过往的高蹈、观照式地书写,回归到更加日常、真实的当下中来,俯下身重又去近距离地还原、去寻找、去揭示这一片所生所长的广阔山海天地。一个具有开阔的诗歌视域与生活体验的厉敏,一个对万事万物悲悯、矜恤的厉敏,他用他独有的视角将自然、时空、物什、事件与精神相互交融,展现着他独特个体的存在感知与精神世界。
厉敏老师的诗歌注重修辞、讲究内在意韵与精神上的提炼,往往都带着哲理和思想的深度,少见语言上的剧烈变化,或者说刻意去强化诗歌语言的“变异”“破坏”性功效,甚至也很少用强烈而直接的自我主体意识切入诗歌的文本,保持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多数诗都是以物以景来引发内心的思考与感悟,以旁观者的视角切入,或是故意保持了这种物我的距离。
虞兵科(省作协会员):厉敏不断在拆解海洋的语言,又不断在重构海洋的语言,他以自己的干净、纯洁、朴素表达着内心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放歌。厉敏的海洋诗歌创作有一个变迁过程,从早期的平铺直叙到后期的意象抒写,两者又互相兼容,呈现了多重的创作风格。厉敏的诗所涉及的题材非常广,他是自由的诗人,写着自由的文字,奔放的,炽热的,喧嚣的,温暖的,嘹亮的,沸腾的,激烈的,宁静的,却是远海之远,天空之上,海岛之角。他的生活是充斥着诗意和硝烟的,他可以完全打开自己的胸膛,数着自己激烈的心跳;他的感情是长满海水和渔火的,他可以完全抛弃自己的内心,径直向东,赴一场海山间的盟约,这是多重风格下的海洋语言的重构景象。但在个性表达的锋芒和锐利上似乎有所欠缺。
吴常亮(岱山作协副秘书长):《厉敏诗选》中,处处透着童话的意境,并用这种意境来重构海洋时空。在《沉锚》,厉敏这样写道:“海就被锚住不动了,一只只生锈的手,要顺着铁索爬上来。”我想像不出这生锈的手是什么,但仿佛又有什么东西现在眼前,正从海中爬上来。《垂钓》开头就说:“抛长长的线于湖中,于心中,垂钓自己……”这需要多大的幻想,多少次的自省,才能写下这样的诗句。在《爱幻想的鱼》中,厉敏这样写:“鱼幻想在大潮的银色大厅里,翩翩起舞,在桂花的驿站,野外的爱情泛起月色。”多么浪漫的一幕,它让我想起美人鱼或灰姑娘的故事。厉敏给人们讲着一个个童话故事,这些故事里蕴含着生活哲理:“我的假期结束了,鱼的戏服也该还了。”
林明忠(省作协会员、嵊泗作协顾问):我与厉敏认识很早,我们一开始都是教育系统的。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厉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将工作与业余爱好兼顾起来,不但书教得好,而且诗也写得好;不但诗写得好,散文也写得挺棒的,真不简单。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譬如,我们同样参加采风活动,他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是阅历不同、角度不同、感受不同等诸多原因;其次,也许某一些事物大家都看到了,却未必想得到,而厉敏想到了我们想不到的东西,这是由于思考的深度和思想内涵上的差异;第三,大家也许都看到了,也想到了,但不一定能表达得出来,而厉敏能却能较好地表达出来。厉敏诗歌具有一些独特性,是他长期历练的结果。
三、诗意呈现与美学追求
缪佳祎(市作协诗创委主任):早期的诗歌,有着朦胧诗的味道,一串串诗行不长,以短句为多,充满着优美的意象和轻盈的韵律,这些诗歌包括海洋诗,都有着唯美的气息,以及对生命的美好期许与眷恋。第一辑中,如《黑的水,白的水》,如散文写作中的排比句式,让人读来有种气势连绵、心神激荡之感。第二辑情感上更显深厚,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与海洋书写的意境渲染中有更多的感悟与思考。第三辑前面两首诗就让人感觉到语言的丰富与新奇,以及诗行间的跨度和张力,大开大合的辽阔气息扑面而来。
正像诗集前言的诗评里写到的那首《海图》,短短一首小诗,却有着宏大的视野与格局。想起上次与来自省城的著名诗人梁晓明、沈苇和飞廉交流时,他们多次提到,海洋、岛屿所延伸的文化创造动力与文学创作魅力,更多的来源于自我生命对所处环境的内在理解,来源于表达自我生命的强烈意愿。厉敏的海洋诗,已隐隐有了这种延展性视角,也就是不限于舟山群岛这个地域性指向,而是趋向于关注人类命运、精神家园的人文性与世界性。
阿能(中国民协会员、省作协会员):我觉得厉敏写诗的时候,往往为一种真正的新鲜而感到心醉神迷,于细微之处见其内在,就像他在诗中那句,似乎还包含了一种小心的伤感美。海岛人面海而生,大海是诗人的一种诗意的宣泄,有一种在平淡的熟悉中嚼出陌生的滋味,品出真实性的哲思,体现了他既传递传统的文化因子,又融入了现代的责任和使命。
清代大画家戴熙曾说:“画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读诗也然。诗歌以汉语独有的韵律美感,承载着绵延千年的情感和文化。读厉敏这些带有节奏和韵律的诗,恰到好处地形容了当时的感受,身之向往心之淡然。在我们静心读厉敏的诗时,任何一个小小感动部分,都会沉思于一片很深的寂静里,这就是诗的魅力。诗人王小波说过:“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读诗,你看见月亮很美,脑子里没词,结果,只能对着月亮说一句:真他妈漂亮。”
梅森(青年诗人):厉敏诗歌《梭子蟹》这首其中的几句:梭子蟹的目光高高举起/它护卫着生存的洞穴和偶然的爱情/无血的肉体穿起骨质的衣服/骨头担心着肉体的诱惑……只有一个人在所处的环境以及生存技能满足时,他才会认识到更多深刻的见解,当然更多的则是思维上带有辩证,质感和历史的认知。再如《鱼贩》这首,从地域上看,叫醒鱼贩的潮水表达贴切,站诗歌角度看到一群人为生活奔波,相反对我而言,叫醒北方土地上的人群则是干涸的土地,更为艰难的则是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如果这是诗歌所表达的东西,进入内心,带来些触动那就是好的诗歌,一首歌的样子一定是精准和流畅的。
岸岛整理

